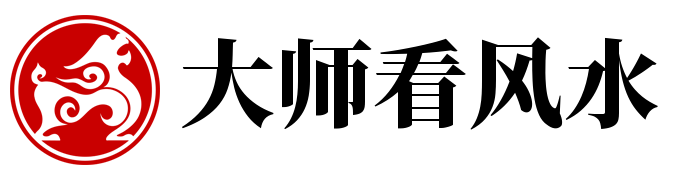诉不尽当年情:七夕,说说88年前金克木的柏拉图爱情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金克木先生旧影。
“织女星在八倍望远镜中呈现为蓝宝石般的光点,好看极了。那时空气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弯,银河灿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上。”
8月4日,又一年七夕。天气炎热,这几天夜里抬头望星,不由想起这个译了《流转的星辰》的星空爱好者,当年,此人译这部天文学译著得了两百块钱,抵得他几个月的工资。他还加入了当时的中国天文学会。
他是金克木。“未名四老”之一的大才子金克木。最近,上海作家黄德海为他写了一本书,《金克木编年录》。
金克木这个人,是个趣人,妙人,痴人,通人。大有说头,今天,我们应着七夕的景,先来说一说“金式浪漫”。
七夕,跟天上的星星有关。我们还难以忘却的,是宋代才子秦观的那一阙爱情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们就来讲一讲大学者金克木的爱情故事吧,或许,他才是最懂得秦观的《鹊桥仙》爱情真谛的人。然而我们今天的人们,会不会赞同他呢?
会不会像我这样,一开始,对他的这种“柏拉图式爱情”,有些生气呢?
【一】
25岁的金克木,生活中的内容除了教书、文学、诗歌,他还是一名星空爱好者。
那一年他迷上了天文学。与朋友一起观星,爱狮子座流星雨,“看了一夜星”。
86岁,“老来观星”。他自况“想不到我的老运忽然亨通一次:今年我望见了海尔-波普彗星,用我的消磨了八十五年的老眼,加上一副陈旧的儿童玩具望远镜”。
到哪里去寻找这么可爱的,有趣的,智慧的老人啊。他比同样有趣的“老头”黄永玉先生还要大一轮,都属鼠。
一个热爱流星雨的人,应该是骨子里有几分浪漫的吧。
他也写诗。
他与诗人戴望舒的友情,持续了终身。他21岁时因为写新诗,就遥识了戴望舒、施蛰存,施蛰存给他写信,说戴望舒和他都看了他的诗歌,很欣赏。就这样由诗而友。1950年,他39岁,戴望舒英年早逝,他参加了诗人的追悼会。
1985年,他74岁,因老友徐迟夫人陈松女士去世,他写了一首绝句寄给悼亡中的老友徐迟。“南浔、香港、莫干山,忽漫相逢五十年。泥上偶然留爪印,莫言天上与人间。”
76岁时,他对忘年交扬之水女史说,“老年人最怕什么?最怕寂寞。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在一起说话的人,而一看见你就觉得很投缘。”
他晚年跟扬之水女史谈到青年时代恋爱事。他虽娶妻生子,妻子的学历比他高,是北大才女,但他又维持了一生的柏拉图式爱情。
这一段柏拉图爱情,发端于金克木的23岁。
1934年春天,他去听法语课,与她初见,出课堂门,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学Z女士手拿着书正站在一边,对我望着,似笑非笑,一言不发。”她的真名,叫卢希微。这一场校园爱情开始萌芽,彼时的金克木,和卢希微同在北京大学旁听法语课。
他们的人生,此后各自转场,相约“做保险朋友”,“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他们通了大量的书信。
他的密友吴宓并不太赞同他谈柏拉图恋爱,还责备了他一通。“在昆明、在武汉,几乎每次提到Z时,他都慨叹说我太不应该,总是我不对。我以为我正是照他的柏拉图哲学实行精神的爱的,为什么反而不赞成呢”?
他既然抱守“柏拉图”,曾多次跟自己的朋友们解释他的这种恋爱。“那是我个人的恋爱,喜欢不即不离。”又说,“若欲使恋爱‘成功’,非用手段不可。”
有时候,他也自怨自艾,给挚友戴望舒写信说:“人生只有生殖与生存,理智和意志从来没用,艺术宗教都是欺人自欺,大家无非是逢场作戏。”这语气,又颇似情场失意之人的牢骚。
这样柏拉图到了30岁,尽管卢小姐屡次曾对金才子倾心,但金克木的态度是,“我决不与伊婚。让伊去嫁她的表兄。故上次伊自日内瓦来函,我复信云:我已死云。——我爱伊深至,为此爱作了这许多诗诉苦。而终不肯婚伊。这样做法,我正可维系着伊对我的爱情。我将随便娶一能煮饭洗衣之太太,买一丫头来做太太,亦可”。
【二】
读到这里,我这现代读者忍不住拍案而起了。这是什么爱情的神逻辑?我都替这位倾心于他的卢小姐不值了,可是,似乎黄德海更理解金克木先生当时的心曲。他替他辩解道:“这个说法,其实是金克木安慰自己啊,他那时候不够自信,所以等于放手让爱人去走自己更宽广的路。这样曲曲折折的心思,最终成就了一段真正的爱情传奇,柏拉图意义上的。”
做《金克木编年录》的黄德海说,金克木的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了他生命的终点,想起来就让人感慨。
金先生与卢小姐,两人鸿雁传书,一直至抗战胜利后,“终于音书亦绝”。想来卢小姐心中的感伤是不少的。但是卢小姐最真实的内心,我们并不知道多少。只知道,逝水流年,卢小姐“感伤复感伤”。
他呢,“她使我在长期乡居中得到安慰,遣除枯寂。”也以“香草应滋九畹好,浮生已觉万缘空”之类的诗句吐露惆怅心曲。
以我们今人的看法,他对她,终究是不够爱吧?然,我们这些现代人对爱情的看法,是否又是一种“俗见”呢?
故事还没有结束。
1948年,他37岁。5月22日,金克木与唐季雍结婚,胡适证婚。这位唐小姐当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是金克木的友人唐长孺的妹妹。
1946年10月,金克木至武汉大学,武大哲学系任教,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并上梵文选修课。武大期间,与唐长孺、周煦良等教授为友。唐长孺在历史系,朋友们常在一起闲谈,忽而旧学,忽而新学,纵横跳跃,不着边际,又是古文,又是外文,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金克木要调到北大去时,唐长孺介绍了自己妹妹给他认识,金克木至北大后,见了唐季雍,两人谈得很好,他们就结婚了。
这是直奔婚姻去的,朋友的妹妹做了妻,这是爱情吗?我们也说不清楚。
“婚后过了几天,我便和季雍同去清华,首先拜访陈寅恪先生并见到陈夫人唐晓筼。”此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婚姻生活,白头偕老了。
唐季雍肯定不止会做饭洗衣,上世纪60年代,他们一起合作了《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唐季雍译,金克木校并作序,可谓“琴瑟相偕”了。
他们有女儿金木婴,儿子金木子。
【三】
金克木77岁时,与忘年交扬之水又谈起与“保险朋友”的这段当年情。这是扬之水的回忆——
“于是与我聊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个恋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年啊,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不过短短一年,那一位就远走他乡,生活在瑞士美国两地,如今只是一年一两张明信片的交往,倘有朝一日再次相传,真是相对尽白发了,这这种可能也是不会有的。”
他们果然一生再未相见。
1990年,他79岁。与扬之水商量卢女士欲退回旧信旧稿事。卢女士因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
他的态度是:“我与他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也是他79岁那一年,夫人唐季雍生病手术,痊愈后他们纪念结婚。金克木作《赠内四首》,其中有诗云——
逝水年华去不还,
愧无一事供开颜。
窗前翠竹早生笋,
不怨人间不怨天。
我在他的诗里,读到的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感情,并没有读出爱情啊。你有吗?相比之下,他因忆及卢小姐而吟出的“林间徒羡双双鸟,梦里难禁漠漠心”、“飞鸿来处无消息,漫对闲云数暮卧鸦”,是否更意味深长?
1993年,金克木82岁。5月,卢希微女士去世。天人永隔。
金克木的一段心语留在了黄德海的《金克木编年录》里,使我们看到了这一位老人的心。
他在《告别辞》中,是这么说的——
“前天才得到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信中只说了年月日,没有说地点是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不过这不要紧。死人的世界是超出时间空间普通三维四维概念的宇宙,是失去时地坐标的。要紧的是死后以什么面目出现。若是离开人世时的形貌,我和她都已经八十岁上下,鸡皮鹤发,相见有什么好?还不如彼此都在心目中想着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在一起谈爱,毫无忌惮。”
我们几个朋友讨论金克木的爱情故事,鲁敏说,爱的最早写法,就是“无心”。在繁体字之前。这是无我之爱了。
才女闫红说,可能他的心思是:这么好一个女人,怎么舍得娶回家当老婆呢?
黄德海说,其实男人的心思,也不好猜啊。
读了这个柏拉图之恋的故事,你认为呢?
1946年10月,金克木(左一)与友人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发布于 2025-01-22 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