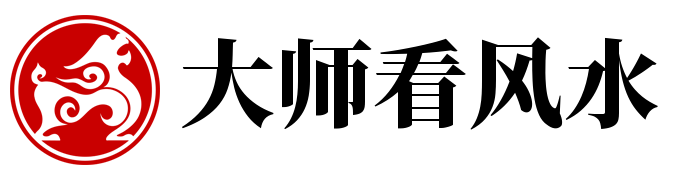我是个命硬的人吗?(第二篇)
写给我娘(第二篇)
我是个命硬的人吗?我不清楚。
时光逆退到四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候距离我来到这人世上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要走,东河岸上的水泥桥把乡村蜿蜒斑驳的土路分成两段,我年轻的娘坐在大马车上面,胶皮轱辘碾过河岸时的颤抖牵扯着她稍微臃肿的身体。马脖子上面的黄铜色铃铛无视夏日午后的沉闷空气哗啦哗啦地响出一条灰白的野道,在我娘往返于这道路两端的夏日里,河岸一侧永远是饱满流淌的河水,另一侧总是绵延无际的蒲草,她早就习惯那伴着村庄历史亘古绵长的胶皮轱辘倾轧在路面挤出的颤抖,可那一日她却从没想到她的儿子会因为这种颤抖在尚未来到这人世之前就已经充满坎坷波折。
野路蜿蜒过村北的土桥,把脸色苍白的我娘送回到土炕上面,她用哀求的目光望向我的那个在我长大的路上几乎从来不管不问的奶奶。那时候纵然生活穷困,可我奶奶却仍然保持着地主夫人的古板,一根长烟袋飘出的一缕细烟勾画出从到晚的全部余生,也冲淡了我娘的哀求声。而那时我的父亲正在生产队马厩旁的羊草垛里睡觉,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二儿子奔往人世的道路将要戛然而止。我年轻的娘泪水滂沱。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勾勒出她为续我一命是用怎样的力气去呼喊住在隔壁的老太太的揪心画面。我是个命硬的人吗?我想我应该是,感谢我娘续我一命。
我在冬日阳光尚未铺满简陋的木窗时哭出声来,宣告着我已经走完了自己前世的全部旅程,我因为眼前的黑暗无光而惊恐,那些围在我身边的人因为我的骨瘦如柴而满含担心地想象勾画着我将来的命运多艰?后来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样聋或者哑,更或者如一团泥巴般堆在土炕的某个角落成为家中愈加贫苦的负累,在他们的目光里我无比倔强地生长,虽然身体瘦削,却依然很张狂地在卷过田野的风里追着车滚草奔跑。可是我在幼年时不定期的抽搐终究还是让我娘满怀心忧。多年以后,我娘坐在菜园边的小木凳上面,说给我当年抽搐到脖子青筋暴突的惨烈故事,我嘿嘿地笑着问她,你就不怕我把自己抽没了吗?我娘轻轻而确定地说,我儿的命硬着呢。时隔多年,我娘能清晰地记得我在锅台前或者大门外精确地点的悲惨画面,因为那个时候随着我脖颈僵直抽搐的还有我娘的心。
几十年过去,我无数次走过村东的土岗,从少不经事奔向五十天命,站在土岗的顶端,能望见土岗下面叶片荒疏但却每年挣扎发芽的老榆树,更能看见穹庐般的天空下每一个季节的颜色,我在那片土坡上沾满季节的痕迹。多年前,我娘也像我这样站在这土岗之上,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季节似乎与她毫无关联,她的目光总在暮色渐起的黄昏里寻找,然后开始呼唤我的名字,等待我从远处的树林里疯跑过来,那时候她衣衫上面正落满炊烟的痕迹。时光行走过几个夏天,我娘那两条乌黑的辫子留在了我少年时代的光阴里,村庄里再也没有马牛嘶鸣的喧嚣,村东土岗下的荒树林翻耕出一片农田,我娘逐渐远离了土岗上面的暮色黄昏,把自己的身影牢牢地印在房前屋后的烟火气息中,年轻时消耗筋骨的辛劳让她身体弯曲脚步蹒跚踯躅,岁月在她手背上沉淀出黑色的斑痕,她开始执着于站在围墙外对空旷田野的遥望,那是她期盼我寒暑易节的归来。
不知从何时起,我娘开始不厌其烦地回忆那些已经走得很远的时光。她坐在老柜子旁,那柜子是她年轻时的嫁妆,她手掌抚摸老柜上陈年的暗红颜色,打开时光里的长镜头说着我年幼时第一次跳上老柜后带给她的愤怒,说着我因为抗拒打针跳窗而逃的顽劣。她的诉说与我知天命的年龄回望的岁月重合,让那样的时光变得无比柔软而悠远。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她身旁,无论生活有怎样的艰辛,我总不会长久地离去,只会顽劣地抖落掉沾满膝盖的泥土去追逐她阳光下操劳的身影。而我长大后回望那些遥远的日子才知道曾经的我娘是多么的艰难,一盒火柴,一支蜡烛,或者生活的琐碎物件儿混在一起,组合成生活里捉襟见肘的穷困,让我娘暗自忧伤,她在那些穷困昏暗的光阴里看着我长大,即使暗自叹息,也从来不把那些昏暗的颜色泼洒向我长大的路上。我在将要知天命的年龄边缘回望,以时光流转多年后人近半生积淀出对生活的感悟去看我娘年轻时的举步维艰,时光仿佛充满了沧桑的硬度。
每一个回家的日子,我娘总是站在院子里对着我笑,她已经很习惯我寒暑易节归来时满脸顽劣笑容的拥抱,就像我年幼的时候习惯于牵着她的手走过门口或者是村北的土桥。我挽住她的臂弯走在人声喧嚣的集市街道上,她放弃了曾经稍显惊慌的挣扎,然后很安心地挪动脚步,接受了自己的衰老。这种衰老让她顾不得白发凌乱而站在门口孤单的遥望,一直遥望到田野在远方溶解出朦胧之色,那是我长大离开时带给她的哀伤。
对于我娘来说,我已经走出一条又远又长的牵挂,那牵挂从我转过墙角离开院子开始,从南瓜的藤蔓爬上后园的柴草堆开始,永远的有始无终。
愿像我这样长大后离家的人,永远是一个被牵挂的人。(祝我娘生日快乐,写于2023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