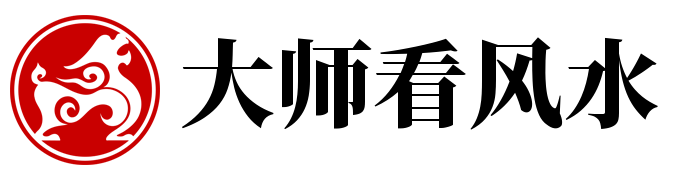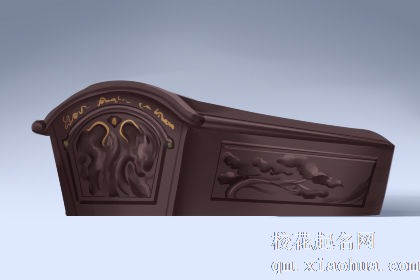袁世凯六姨太悲惨晚年:死后买不起棺材,谁知银行存有巨款
袁世凯六姨太悲惨晚年:死后买不起棺材,谁知银行存有巨款
在民国动荡年代,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曾是南京叶家的千金小姐,更是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然而命运弄人,原本该嫁给年轻英俊的袁克文,却阴差阳错成了其父袁世凯的第六位姨太太。从此,她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袁世凯去世后,这位曾经锦衣玉食的六姨太,最终沦落到连棺材都买不起的境地。更令人唏嘘的是,在她去世后不久,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却传来消息,说她在行内存有一笔数额惊人的存款。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人生悲剧?这笔巨款又是从何而来?
一、南京叶家千金的沦落
清光绪十七年,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畔,叶家大宅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这一日是叶员外的掌上明珠叶蓁满月之喜。江宁商会的显贵、秦淮河畔的名流纷纷前来贺喜,热闹非凡。
叶家在江宁城经商已有百余年,专营丝绸、茶叶贸易。叶蓁的父亲叶庭训,凭借祖辈积累的人脉和自己的经商才能,将生意做到了苏浙皖三省。每年光是经手的丝绸就有数万匹之多,茶叶更是远销俄国。
在这样的富贵之家长大,叶蓁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她不仅精通琴棋书画,更跟随江南名儒学习诗词歌赋。每逢花朝月夕,秦淮河上的画舫中常能听到她的琵琶声,悠扬婉转,令人心醉。
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列强借机在华驻军,外商纷纷撤离。叶家的茶叶生意一落千丈。紧接着,太平天国战乱的余波又让江南丝绸业遭受重创。叶庭训四处借贷维持,却终究难敌时局。
一日,叶庭训正在清点账目,突然口吐鲜血,倒地不起。几位大夫轮番诊治,却都无能为力。临终前,叶庭训将叶蓁唤到床前,将一串祖传的玉珠交给她,说这是留给她日后防身之用。
叶庭训去世后,叶家的生意落入叶蓁几个兄长手中。这几位少爷平日只知吃喝玩乐,哪懂得经商之道。不到半年,就将几间绸缎庄典当一空。更有甚者,竟将祖传的大宅也输在了赌场。
叶蓁的大嫂见家道中落,便挑唆丈夫将叶蓁赶出家门,说是养不起这个妹子。无奈之下,叶蓁只得投靠母亲的娘家。谁知母族亦是家境清寒,难以相托。
就在此时,秦淮河畔一家名为"听雨轩"的青楼老板娘找上门来。这位老板娘年轻时也是名门闺秀,因家道中落而落脚风月场。她看中了叶蓁的才情,愿意收留她。
在那个时代,一个富家小姐沦落风尘,无异于天塌地陷。但为了活命,叶蓁别无选择。所幸"听雨轩"不是寻常的烟花之地,更像是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叶蓁以"梨花仙子"为名,专事吟诗作画,从不轻易见客。
叶蓁的诗画很快在秦淮河畔传开。她的《春江花月夜》一诗被文人传抄,画作《江南春雨图》更是被南京知府收藏。一时间,想要一睹叶蓁风采的达官显贵络绎不绝,却都被她婉言谢绝。
二、成为六姨太的转折
光绪三十一年初春,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来到"听雨轩",自称袁克文。几位老主顾见了他,纷纷起身行礼。原来这位少年正是当朝重臣、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次子。
那日,袁克文本是奉父命来南京办事。事毕之后,听闻"梨花仙子"的才名,便慕名而来。叶蓁正在厅中抚琴,一曲《广陵散》行至中段,袁克文便随手援笔,写下一首《听琴》:"十弦清越动春风,不解愁心付玉笻。谁道江南无旧曲,夜来还听广陵钟。"
叶蓁见袁克文诗才不俗,便破例留他饮茶。二人对坐谈诗论画,从《诗经》谈到《楚辞》,又从李白谈到苏轼,竟是知音难觅。一番畅谈,直至更深。此后三日,袁克文都来"听雨轩"寻访叶蓁。
临别前夜,袁克文向叶蓁吐露身份,许诺待回北京后便向父母求亲。叶蓁本想婉拒,却被袁克文的诚意打动。不料这一诺,却引出一场惊人的变故。
袁克文回京复命时,从怀中掉出叶蓁的画像。袁世凯拾起一看,只见画中女子眉目如画,气质雅致。袁世凯细问之下,袁克文慌乱之中,竟谎称此女是为父亲特意物色的良配。
袁世凯大喜,当即派人前往南京,要将叶蓁迎娶为第六房姨太太。袁克文欲言又止,终究未敢违抗父命。十日后,叶蓁便在袁府办妆。
成亲那日,叶蓁坐在八抬大轿中,一路鼓乐喧天。待到洞房,掀开盖头,却见新郎竟是年过半百的袁世凯。这一刻,叶蓁只得强忍泪水,拜堂成礼。
入府后,袁世凯对这位才貌双全的六姨太格外宠爱。叶蓁不仅精通诗词,还擅长针线女红。她为袁世凯绣的一幅《山水清音图》,被袁世凯赞不绝口,还特意装裱挂在书房。
袁世凯常与叶蓁对诗饮茶,两人合作的《春日南园即景》一诗被文人传诵。叶蓁更是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将袁府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采买、账目,还是下人调遣,都让袁世凯十分满意。
然而府中妻妾众多,难免有些明争暗斗。大太太沈氏虽表面客气,却常在背后使绊子。三姨太张氏更是嫉妒叶蓁受宠,时常在袁世凯面前搬弄是非。所幸叶蓁处事圆滑,既不与人争锋,也不卑躬屈膝,渐渐在府中站稳脚跟。
叶蓁为袁世凯生下三女二子:长子袁克捷、二子袁克友,以及袁福祯、袁奇祯、袁瑞祯三个女儿。每当叶蓁带着孩子们在后园嬉戏,袁克文远远望见,总是默默转身离去。这段原本该有的姻缘,终成了府中一段不能说的心事。
三、袁世凯之后的家产纷争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逝于北京。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北洋军阀,留下了庞大的家产,却也埋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纷争。
遗产分配当日,袁府大堂内人声鼎沸。袁世凯生前立下遗嘱,规定每个儿子可得现金一万元,外加股票和房产。女儿们只得到少量现金。至于姨太太们,按照当时的规矩,竟是分文未得。原本锦衣玉食的叶蓁,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
袁府总管申明善手持账本,宣读遗产分配细则。此人在袁世凯在世时就擅长溜须拍马,如今掌管着大部分子女的遗产,更是趾高气扬。当着众人的面,他对叶蓁说道:"六太太,您的子女所得遗产,还需由我代为打理。"
叶蓁本想据理力争,但在场的袁家子弟无人为她说话。大太太沈氏的长子袁克定更是冷眼旁观,似乎在看一场好戏。就这样,叶蓁子女的遗产落入了申明善之手。
不甘坐以待毙的叶蓁决定自己创业。她变卖了几件首饰,在天津租下一间绸缎庄。凭借着在江南丝绸之乡的见识,加上自己的经营头脑,初期生意倒也顺遂。然而时局动荡,加上申明善从中作梗,不到半年,绸缎庄就开始入不敷出。
正当叶蓁为经营发愁时,突然得知一个消息:申明善暗中勾结天津当地的商人,抬高丝绸进货价格,还散布谣言说她的绸缎庄商品质次价高。一时间,客人纷纷退避,生意一落千丈。
到了年底结算时,申明善拿着一本记满红字的账本来找叶蓁。他说道:"六太太,您的子女信托给我的资产,已经损失了大半。这是明细账目,请过目。"叶蓁接过账本一看,上面尽是些模糊不清的数字,显然是做了手脚。
无奈之下,叶蓁只得变卖袁世凯留给子女的几处房产。其中一处位于天津意租界的洋房,本值万金,却被申明善以"市面不好"为由,贱价卖给了他的亲信。更让叶蓁愤怒的是,那处房产在半年后又以三倍的价格转手,申明善从中获利巨大。
面对如此局面,叶蓁四处投诉,却都石沉大海。大太太沈氏对此事避而不谈,其他姨太太们也都噤若寒蝉。就连一向疼爱她的儿子袁克捷去找申明善理论,也被对方以"军阀后代"相威胁,不得不偃旗息鼓。
此后,叶蓁家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绸缎庄倒闭后,她又尝试开设茶馆,效仿从前在秦淮河畔的经营方式。但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周转,无奈她的娘家人又是花钱如流水,短短几年间就将最后的积蓄耗尽。
人走茶凉,世态炎凉。昔日那些在袁府门前献媚的商人、官员,如今见了叶蓁都是绕道而行。一时间,叶蓁家中断炊之事时有发生,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四、生活的艰难与挣扎
申明善卷走家产后,叶蓁一家的生活全靠子女接济。次女袁奇祯在天津一所师范学院任教,每月工资三十元,省吃俭用给母亲寄去二十元。三女袁瑞祯因战乱去了台湾,偶尔能托人捎来一些生活用品。至于长女袁福祯,早年便已夭折。
这时的长子袁克捷刚从南开大学毕业,本想在天津谋个体面差事。但他一报出袁世凯的名字,便吃尽闭门羹。最后只得在街头摆摊卖些零嘴糖果,日进斗金的袁府公子,沦落到为三餐奔波的境地。
1950年,政府开始清查旧军阀财产。叶蓁居住的天津老宅也面临查封。此时,宁夏银川一位叶蓁的远亲得知消息,邀请他们全家迁往宁夏。袁克捷带着母亲和两个儿子,离开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天津。
银川的生活清苦,但总算安稳。政府体恤他们的处境,分给一间两进的小院,每月还提供一些口粮。袁克捷也在当地找到一份搬运工的活计,虽然辛苦,但总算能养家糊口。
叶蓁从小娇生惯养,一双"三寸金莲"走路都费劲,更别说干农活了。但她并未因此自暴自弃,而是在家里纳鞋底、织毛衣贴补家用。街坊邻居都说,这位老太太虽然举止优雅,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让袁克捷感到欣慰的是,母亲虽然生活落魄,但读书看报的习惯始终没改。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母亲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戴着一副老花镜读报纸。只是烟瘾依然很大,每月光买"耕牛"香烟就要花去不少钱。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的一个夏日,袁克捷在搬运木材时,被一根倒下的圆木击中后脑。等工友发现时,他已经没了气息。
这一变故,对叶蓁的打击极大。她整日坐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包"耕牛"牌香烟,目光呆滞地望着大门口,仿佛在等待什么人。街坊们劝她出去走走,她只是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当地政府因查清袁克捷家的成分,停止了各项救济。叶蓁一家顿时陷入困境。两个孙子为了生计,整日在街上拾破烂、捡煤核。那些曾经对他们客客气气的邻居,也开始对他们横眉冷眼。
一天傍晚,小孙子从街上回来,发现奶奶倒在炕上,已经断了气。临终前,叶蓁还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当年在秦淮河畔"听雨轩"拍下的。照片背面写着一首诗:"十年身是凤凰人,又作江南寒燕飞。最是天涯沦落处,谁怜今夜雨斜时。"
五、悲惨结局与未解之谜
叶蓁去世那天,银川城正下着小雨。两个孙子手中仅有的几块钱,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最后只得用几张草席将祖母裹住,匆匆埋在了城郊的公共墓地。与其父袁克捷一样,这位曾经的袁府六姨太,临终连一块棺木都未能享有。
叶蓁下葬后第三天,一封来自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信件送到了银川市政府。信中称,叶蓁在该行尚有一笔数额可观的存款,需要本人亲自前往办理支取手续。市政府派人找到生产队,当地干部只得告知叶蓁已经去世的消息。
这封信很快传到了天津的袁奇祯耳中。这位在师范学院任教的次女立即向银行提出继承请求。然而,银行方面以"手续不完备"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
一个月后,叶蓁的两个孙子带着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文件,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他们在中国银行总行等候了整整三天,才见到负责此事的经理。这位经理翻看了他们的证明文件后,却说需要更多的公证材料。
就在两兄弟准备返回银川办理公证时,一位姓赵的老职员悄悄告诉他们:"你们祖母在1916年,也就是袁世凯去世那年,曾在本行存入一批金条和银元。当时全权委托给一位姓周的先生代为保管,约定非本人不得支取。"
这位周姓先生是谁?为何叶蓁生前从未提起过这笔存款?两兄弟带着疑问,开始四处寻访。他们找到了当年在袁府任职的老仆,得知在袁世凯临终前,曾秘密召见过叶蓁。当时府中只有一位姓周的老管家在场。
更令人费解的是,银行的存款凭证上有一个特殊的图章,那是一个篆刻的"听雨"二字。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叶蓁年轻时在秦淮河畔"听雨轩"的经历。难道这笔钱与她的青楼往事有关?还是另有隐情?
这笔存款的数额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是个谜。有传言说是黄金千两,也有人说是百万银元。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为何叶蓁宁可清贫度日,也不去支取这笔钱?这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后来,叶蓁的两个孙子在多方碰壁后,也放弃了继承这笔存款的打算。大孙子去了内蒙古,在阿拉善盟成了一名牧民。小孙子则回到银川,在当地林场当了一名伐木工。至于那笔存款的命运,至今仍是个谜。
在银川城郊的公共墓地里,叶蓁的坟头早已长满了荒草。每年清明,附近的老人还会给这位不知名的老太太上一炷香,只因为她生前经常给村里的孩子们分糖果。而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袁府六姨太"的身份,也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被人遗忘。
微信分享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