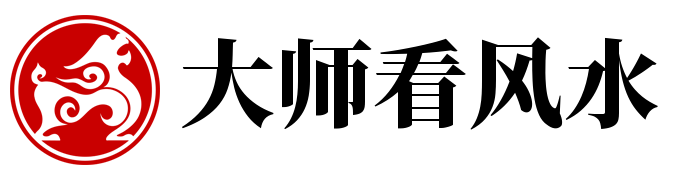一个人的命运可以有多悲惨
舅母死了
听母亲说,大表嫂托人告诉她,舅母不在了。我听了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对于只能用悲惨来形容的舅母来说,死,也算是一种解脱,一种从躯体到心灵的解脱,也好在那边和她的不怎么样的丈夫、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汇合,享受生前没有享受的乐趣(或许,从我舅舅和她的两个儿子的生前表现,够呛)。只留下她远嫁的小闺女在人间。
说起舅母,基本上是个悲惨的故事。
次序不能乱,要想有舅母,就一定得有个舅舅才行。说起舅舅,其实也不是亲舅舅,这个舅舅是母亲大伯的儿子。
据说外公在外出做生意的时候,算了命,算命先生说,外公只有结婚三房,才能落一枝花。外公也是信——命中还真是这个样子:外公结婚三次,于是我就有了三个外婆(也就是旧社会有钱人家的三妻四妾)。但在外公和第三个外婆结婚的时候,家道已经没落,只能退而求其次,第三个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亲妈——据我母亲说,是和外婆的爹妈到外公那里要饭,外公给外婆的爹妈养老送终,外婆就嫁给了外公。并且这个外婆的脑子是不大灵光的。
外婆和外公结婚后,就生了母亲和小舅(不是这个舅舅),小舅随外婆,也是傻傻的,在六零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就饿死了。
而这个舅舅,不知道是生了小舅后看小舅傻,把他过继给了外公,还是有了母亲后,听信了那个算命的说法,过继给了外公。这些也不是什么大事,与本文无关,这里也没有深究。
外公的地主成分,在解放前,就已经开始没落,解放也就是雪上加霜而已。到了解放的时候,要是根据占有地的多少来划分地主,外公家根本就不够资格,之所以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完全是他们庄上实在挑不出比外公更有钱、地更多的的人家,算是瘸子里面挑将军了——没落地主竟然还能在庄上撑起地主的架子,也只能说是这个庄上的悲哀。
更悲哀的是舅舅,本来是根正苗红的贫农,现在成了根不正苗还黑的地主,没有享地主的福,却要受地主的罪。所以,自从舅舅懂事起,就开始闹着要脱离地主家庭,回归本家。
但哪里有那么容易,这边两个老地主——外公和外婆(不是母亲的亲生母亲,外公的第一个老婆,另外两个外婆,解放后,由于新社会,就被遣散了),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地主(我母亲),虽然好欺负,但实在是太弱,勾不起兴趣。好容易有个身强力壮的能欺负的,哪里能让他轻易跑了。于是舅舅虽然一直想回归本家,但一直没有实现。
于是舅舅就逃走,出门就跟人学了篾匠,跟着师傅走南闯北,整天不落家。不知道是老师教的好还是舅舅在这方面就有天赋,舅舅的篾工远近闻名,妥妥的一个好篾匠。据说,舅舅用竹子编出来的竹席,薄,并且韧性十足,可以像纸张一样叠叠装到口袋中。从地主到一个很好的手艺人,这是不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
家里只剩下两个老的和一个小的,硬顶着地主的帽子苦熬着。
据母亲说,六零年的时候,不是地里的收成坏,而是大炼钢铁把各家各户的铁器包括锅碗瓢勺收上去,拿去炼钢,吃大锅饭又少的可怜。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都吃不饱,他们这些需要改造的地主能不被饿死,算是万幸了——小舅被饿死算是在计划范围内。
于是要想不挨饿,不被饿死,只有在夜里行动,不管是红薯、嫩玉米穗、还是豌豆荚,只要能不生火(砸锅炼钢,吃大食堂不让家里冒烟做饭)还能饱肚子的东西,都成了首选。
外公是信主耶稣的,奉行不偷盗的作风,但眼看要饿死,对老婆女儿的半夜行动也就默许了。但耶稣对于他的虔诚信仰,也不另外照顾他:外婆偷了一次,被村里的干部逮住,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卧床不起(和她一起去偷的女人,被逮住了,是可以原谅的;地主和地主婆本来就是被改造的对象,成了小偷就更要加强专政)。于是拯救这个家庭三个人的生命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母亲身上。
“吃过晚饭,就有许多大姐大嫂来喊,让和她们一起出去。我会说:我不敢去,你们去吧,人家逮住了打。大家都知道,逮住了,那些贫民是没有事的,我这个地主崽子就少不了挨打的。等人家都走了,夜深人静了,你外婆就把裤子的两个腿用绳扎起来,两边搭在肩膀上,就像驴子干活时候,怕被缰绳磨破皮的护肩。”母亲现在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和,像给我们讲故事,讲别人的好像与她没有一点关系的故事。
“到了地里,只要遇到能吃的东西,不管是红薯,还是嫩玉米,还是豌豆荚,实在没有什么吃的,就揉麦子吃,总之,先吃饱了再说。吃饱了,就往裤子的两条腿中装,装满了,到庄边看看没有人了,才敢回家。到家,那时候你小舅还没有饿死,三个人吃饱才睡觉。
你外公饿的浑身浮肿,不敢吃生东西,你外婆就用家里唯一一个没有被摔的瓦罐,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煮熟让你外公吃。
那时候,你小舅,五六岁了,饿的脖子支撑不起头。人也有点傻,架不住饿,后来就饿死了。
有一次,我在地里,两个裤腿已经装满了。可一下子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不知道哪里是回家的路。又不敢喊,又没有人问,四面漆黑一片(“奶奶,你不会看北斗星,不就知道方向了。”儿子在旁边说)。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哪里知道什么北斗星呀。后来冷静下来,顺着麦行走,总能走到地头吧。
到村庄上的时候,已经半夜了,你外婆站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一看到我,抱着我,就哭了起来,还不能出声哭,害怕人家听见呀。
别看我那时候小,那时候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呀。”
母亲往往以骄傲结束。
舅舅那时候走南闯北,由于有个过硬的技术,吃香喝辣的,一边还在闹着要脱离这个地主家庭。
“我对于你这个舅舅,最感动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就那一次,感到他和我还算是兄妹,在他的心中还有他这个妹子存在。
那一次他从外地回来,人家穿戴整齐,红光满面的。到了村边,见到我,看了半天,问:你是不是兰(我母亲的名字)呀?我木然的看着他。待确认后,抱着我就哭了起来。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饿的皮包骨头,穿的破破烂烂,蓬头垢面的,你舅舅竟然一下子没有认出来。毕竟在一个锅里搅勺子那么多年,还是有点感情。估计那一次,是真伤心。”
舅舅不知道是本性如此,还是在外面混的如此,“好吃好喝,并且是长头发迷”,这是我妈对她找个哥哥的评价,“长头发迷”说白了,就是喜欢和女人打成一片。
这三个习惯(也算是毛病),使舅舅在外边不知情的人那里混的风生水起。舅母的父亲就被还算一表人才的舅舅给忽悠了,承诺要给舅舅介绍个媳妇。
舅母的父亲,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但这个出名,并不是当官,也不是有钱,而是说媒。
人家说媒,那真叫一个专业。据说,周围十里八村(那时候的人,也就在那么大的地方转悠)的未婚但已经到结婚年龄的男女,有权的和有权的,有钱的和有钱的,俊的和俊的,丑的和丑的,有钱有权的俊的,有钱有权的丑的,没钱没权的俊的和没钱没权丑的。。。。。。都在人家的脑子中装着,什么样人和家庭相配合适,人家更是专业级别。
并且不像现在,男多女少,媒人的要价也水涨船高、明码标价。那时候说个媒,也就是吃顿饭,逢年过节了,拿个礼串一下就行了。
哪家的姑娘不嫁人?哪家的小伙不娶亲?并且都想找一个门当户对、人貌相当的。于是,舅母的父亲就成了十里八村的红人。
可是,到了舅舅这里,事情就成了意外。舅母的父亲给舅舅介绍了很多,就是怎么也不成,不知道是月老的线没有搭上,还是舅舅在外面混的风生水起在这十里八村就失灵了。
出了名的媒人,不能就这样翻船了,一赌气,就把自己和舅舅年龄相当的大闺女嫁给了舅舅——不能把媒红的名声掉地上。
和舅舅结婚后,生了四个儿女,老大老二是两个表哥,老三老四是两个表姐。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年代,这样的配置也算是比较简配的标配了。
有儿有女的这样的双好,也没有使经常浪荡在外的舅舅收心。虽然作为一个好篾匠,挣钱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架不住他的好吃好喝,在女人方面更是无底洞。
于是,舅母在家里拉扯着六个人的土地,艰难的生活着,舅舅在外面挣钱挥霍着,到舅母这里,就所剩寥寥了。
舅母就一边种着地,一边养活着四个儿女,一边等着那没有希望的希望,但往往,等来的就只有失望。
那时候,外公已经去世了,剩下外婆和舅母母子生活。舅舅是那个样子,想舅母对他的母亲多好,也是想想算了。外婆对于舅舅,虽然把他养大,但地主的帽子也把养活的恩情抵消了,舅舅和外婆的亲情关系,也是不怎么凑合。
那时候已经摘了地主的帽子,外公还留下一大片宅基地,母亲已经嫁给了父亲,也没有人给他争家产。闹了许多年的回归本家也告一段落。
虽然身在新社会,人在屋檐下——外公过世后,这个家就成了舅舅和舅母的家,但外婆依然还秉承着地主婆的习惯,要强,不认输,没个笑脸。与舅母的关系可想而知。
于是,外婆就到了我家。人常说,生个好儿子不如娶个好儿媳妇,生个好女儿不如嫁个好女婿。父亲虽然许多地方让人诟病,但对待老人的地方,还真让人没法说。
外婆在我家住了十一年,偏瘫在床上三年。自己有儿子,老人是不能老在闺女家的,最后,眼看不行了,就拉回了舅舅和舅母家。拉回去一个多月,外婆就去世了。
“要是在咱们家,你外婆起码能多活几个月的。”母亲提到这个外婆,总是伤心的说。
这中间,我和母亲去过一次,看着外婆瘦骨嶙峋的身上,我当场就哭了起来。
只有我和母亲的时候,外婆从被窝中摸出一个个的馒头疙瘩,放在母亲手中,有气无力的说:“拿回去喂咱们的鸡子。”
敢情,他们谁也没有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家人。
舅舅在外婆过世后,好像也感到过意不去,毕竟不管怎么样,我外婆和外公把他养大,并且把家产都给了他。可外公好像没有怎么照顾,外婆又在我家住了十一年,即使作为继子,也没有负到自己应有的责任。
于是竟然破天荒的找人和我父母商量,说是把外公留给他的宅基地和母亲平分了。母亲颇有点女侠的气概,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外公留给舅舅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只希望他和舅母过的好就行了。舅舅就有了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惭愧。母亲在娘家达到了很高的声誉。
但舅舅和舅母哪里能过好呢。舅舅还是那个样子,好吃好喝好女人,在外挣的钱,大多数花在了个人爱好上。有时候来到他妹妹这里,和我母亲或者父亲谈起来,也是悔不当初,好几次竟然流下了悔恨的眼泪。但他的悔恨就像小孩子的悔恨,来的快去的也快,一转脸,依然我行我素。
舅母呢,只好带着四个还在苦撑着。
反过来,舅舅还说影响了自己的幸福,有几次准备和舅母分开过——也没有说要离婚。比较木讷的大儿子和大闺女分给舅母,他认为机灵的二儿子和二闺女分给自己。让我母亲和父亲逮住他好一阵说,一家子才恢复原状。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过着。波澜起伏、酸甜苦辣。
舅舅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得了食道癌,那时候我还小,况且还在上学。听说舅舅疼的厉害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用棍子照脊梁上打,用打木来缓解疼痛。
不到一年,舅舅就离世了,算是对自己的解脱,更是对舅母的解脱。虽然当时四个孩子都不大,但两个表哥已经能自食其力,两个表姐在上学之余也能帮舅母分担一些。舅舅对于这一家人的贡献,也就是组织这一家人吧。
舅舅过世的当天,被他看重的二表哥是说什么也不勒白头,任凭舅母把棍子打断,也没有流一滴眼泪。二表哥说,他这个父亲,从来没有对这个家负责过,并且一手好篾活也没有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这样的父亲,不值得哭。
人做到这个份上,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爹的孩子早操心。原先舅舅在的时候,对这个家庭就没有怎么负起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舅母娘儿五个也没有怎么指望他。现在更是靠山山到、靠墙墙塌,只有靠自己了。
好在两个表哥虽然摊上这么个父亲,就格外的争气。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涯,不但都娶妻生子,并且在村子里气气派派的各自盖起了各自的房子。据说当时,弟兄两个的房子在村子里是数得着的。舅舅在世和去世后,这个家庭在村里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次。虽然在我看来,弟兄两个有虚荣和显摆的意思——意思是别看我弟兄两个,虽然没有父亲的帮衬,只靠我们自己,也能过得风生水起,让那些原来看我们或者准备看扁我们的人看看。
但舅母,还没有从喜悦中国反应过来,就开始了又一轮的难受。
作为女人,像母亲这一代人可以说,在历史上都是让上帝抛弃的一代人。因为作为儿媳妇,封建家长制度的余威还在,那些婆婆算是“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了,在自己婆婆那里受的罪要从自己儿媳妇那里找补回来。等到自己“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了,又到了儿媳妇翻身解放的时候,儿子们大多也成了帮凶的白眼狼。算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
舅母虽然没有怎么受过婆婆的罪,但自己的丈夫算是代替婆婆,把本来需要在婆婆那里受的罪,一点也没有落下。在媳妇这里,虽然没有亏,但补还是补不回来
大表哥比较实在,娶的大表嫂子,在大表哥的潜移默化下,也说的过去。二表哥本来就比较灵活,娶的二表嫂子就只能用彪悍来形容。
大表哥结婚之后,生了一个闺女,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再生了,随后抱养了一个儿子。两口子为了两个儿女,在山东打工,给老板切石头,听说还挺能挣钱。但最后大表哥算是死在这个工作上。
二表哥,在山东的一个机械厂,通过努力,竟然混到了管理层。在农村也算是还可以了。但二表哥继承了舅舅的“优良传统”,但二表嫂就没有了舅母的软弱,不但把二表哥拾掇的虽有贼心、但没有贼胆,并且就像裤袋一样拴到了二表哥的身边,严防死守,以防不测。并且这也算是二表哥一个短处,捏在二表嫂手中,经常把二表哥骂的像三孙子,哪里还敢有异心呀。两口子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后,计划生育那么紧,也是二表哥枪法准,二表嫂在带环的情况下,又生了一个闺女。
弟兄两个各自轮半年养活老母亲。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中国,家庭的不幸,基本上都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矛盾造成的——婆媳矛盾。
于是,在几乎每一年去外婆家拜年,都是听舅母和二表嫂的老生常谈:二表嫂是一边诉苦一边破口骂的,说是老大两人会舔舅母,舅母对老大家好,对他们这个老二,就像不是亲生的,不管是生活中帮忙,还是照顾孩子,还是有什么好东西,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他们。
舅母呢,也不管是应该喜庆的大过年,老是眼泪八叉的,和母亲诉说老二媳妇的霸道和老二的不作为。老大两口子只说好的事情,糟心的事情都埋藏在心里——也知道,把事情告诉他们这个一年见一次的姑姑,也无济于事。
真不知道,平常在没有人诉苦的时候,舅母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母亲呢,把什么都看的很开,知道自己在这样的关系中,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最多就是当个排气扇,让别人排解下憋了一年的气罢了。当着任何人的面说谁的不是(即使是自己的侄儿和媳妇),都会造成最起码的隔阂。不如双方解劝一下,让双方宽宽心,至于对方能理解多少,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了,不是这个外人能左右的。
陆续的,两个表姐也结了婚,大表姐嫁到的他们附近的村子,二表姐就远嫁到了山西。
这样过了十多年,有一年听父母说,舅母去小闺女那里,改嫁了。听说那个男人老婆去世了,是村支书。对舅母很好,对方的儿女们对舅母也还行。并且人家每一年给舅母存一笔钱,意思是就算是老头到时候走在舅母前面,儿女们对舅母不好,起码舅母的生活还是有保证。
“唉,你舅母可算是到了享福的时候。”父母每每谈到舅母,都会这么说。
有一年,半路碰见舅母(回来探望儿子和大闺女的),感到舅母脸上也有了原来没有的光泽,精神状态也比原来好多了,眼上由于得了青光眼带上了眼镜,比原来多了一些气质。
每一年去母亲娘家拜年,二表嫂的骂声里又有了新的的内容。舅母增加了“不要脸”的罪名,小表姐成了“没安好心的死叉子”。大表哥和大表嫂老是说,“不管怎么着,只要我妈过的好,比什么都强。”
虽然骂舅母和她的小女儿是每一年去母亲娘家拜年,二表嫂的保留节目,但日子平平静静的如水流过,没有波澜。
平静的日子过了五六年。这五六年估计是舅母过的最舒心,最幸福的日子。
“你舅母回来了。”有一天,母亲告诉我说。
“那边老头死了?”我意外的问。
“没有。”
“那她回来干吗?”根本想不出舅母回来的理由。
“你舅妈说,家里儿孙满堂的,走这一步嫌丢人。”
唉,不知道这个舅母怎么想的,连毛主席都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的无奈。爹死娘嫁,仅仅是一个女人出嫁的问题,根本就牵扯不到丢人不丢人的问题。
况且,即使另嫁,自己嫌丢人,可已经嫁了,已经丢人了,已经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了,已经落下把柄了。现在回来,也改变不了什么呀?何必要回来呢?为了一个自己和别有用心的安嫁的莫须有的“丢人 ”罪名,搭上受了半辈子罪换来的迟到的幸福,何必呢?
现在,两个表哥是一轮一年的照顾舅母,那一年轮到的表哥,两家公共的客人,过年的时候就到轮到的表哥家里做客。
忙现在是大家的常态,基本上就是一年一次,正月初三去母亲娘家拜年。舅母这一次回来,早没有了原来的态势,原来还和母亲诉诉苦,拉拉家常,现在好像要弥补这几年没有在家对两个儿子的亏欠(其实也没有什么亏欠,不过是她自己心里觉得而已),每一年,不管是轮到大表哥家还是二表哥家,基本上都是在厨房忙忙碌碌的,大表嫂还稍微好些,只是让干活,看着有客人的份上,起码嘴里干净。二表哥家里舔了儿媳妇和孙子,两个闺女也是吃净饭的主,根本不插手。于是,厨房中,就自由舅母始终忙着,表嫂忙过后,还要去客厅尽地主之谊,舅母舅只有坐在灶台边抽空吃上一口,配菜就是二表嫂的训斥。
但看舅母,好像还挺满足。
这样的日子,在舅母那里,好像也说的过去,人老了,哪里还能有那么多的要求呢?儿孙满堂,虽然儿媳妇不怎么着,但儿子还说的过去;虽然挨训,但好在是一家子在一起,起码不让人捣着脊梁骨生活(其实原来也只是她自己以为的,没有人好事到去山西捣她的脊梁骨的)。
但厄运笼罩着还没有安生几天的舅母的儿女身上。
首先是大表姐。
作为普通人,就得个普通人能得的病就得了,谁知道,大表姐竟然得了只有传说中、只有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才能看到的疾病:肌肉萎缩,并且不是腿,不是胳膊,不是能运动的腿和胳膊,而是全身,全身都肌肉萎缩。
在舅母没有远嫁山西的时候,大表姐就开始表现出了症状。这个病的最可怕之处就是,即使把人判了死刑也是循序渐进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作为一个那时候还没有国家医保的农民,只能把一家子挣的钱全部慢慢的、像钝刀割肉似的全部送到医院中,接着一家子再挣钱,再往这个看不见底的无底洞中投。
那是个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个一家子最亲的人,不能眼看着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只能强忍着贫寒,强忍着越来越贫寒,尽最大努力医治着。
一直到舅母从山西回来,大表姐又坚持了2年,才解脱,这种解脱,不但是她的肉体精神的解脱,也是一家子的肉体精神的解脱。
据母亲说,大表姐临死的时候,身上基本上没有一点肉了,全身的肌肉萎缩贴在骨头上,没有一点水分光泽的皮肤贴在萎缩的肌肉上,简直就是一具骷髅。
二表哥的死,完全是个意外,按身体条件,按精神状态,按死亡排序,是根本轮不到他的。谁知道就偏偏轮上他了。
2020年春节的新冠疫情,把大家都堵在家里,当然也包括一直在外打工的二表哥一家子。
过了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终于解封了,着急出门打工挣钱的二表哥,急匆匆的骑着摩托要到镇上去办防疫证明。谁知道证明办好了,在回来的路上,和迎面而来的另一辆摩托车相撞,当场就把二表哥给撞死了。
后来经过查证,对方是酒驾,并且负全责。但同样是打工的农村人,你不可能让对方赔付太多的损失——具体也不知道赔多少钱,反正不多。
而这赔付不多的钱,又引起了不必要的龌龊。据二表嫂和母亲说的,庄上的一些鬼,说是二表哥的赔偿费,舅母也有一份的,并且大表哥和大表嫂也这么说的。对于别的鬼,二表嫂只是骂骂过过嘴瘾,对于大表哥和大表嫂还有当真的和二表嫂提过一嘴的舅母,就成了仇。
“我这可是死人的钱,死人的钱也要,还是人吗。我家的顶梁柱不在了,已经够伤心了,还要在伤口上撒盐。作为亲妈,作为亲大哥亲大嫂,和那些鬼一样看笑话。是人能干出来这样的事吗?”当然,二表嫂在和母亲说的时候,是破口大骂的,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的骂(在这方面,二表嫂的嘴是真不是嘴,喷到谁的身上,只有臭的份)。
大表哥的死,是早就有了反应的。
一直以来,大表哥都是在山东打工,给人切石头。切石头虽然很能挣钱,但标准是重体力的活,同时,经常切石头时候漫天飞舞的石粉,很容易钻入人的肺中,就形成了传说中的矽肺。而农村人,根本不懂个人防护,况且那时候还年轻,有的是精力,没明没夜的干,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开始表现是气力跟不上,就少干一点吧;接着就表现浑身没有力气,那就回家不干了;最近几年,渐渐的连走路都感到吃力了。
2021年,大表哥也过世了。
不到两年时间,两个儿子相继过世,对舅母打击可谓大。在这样的常人难以忍受的强烈打击下,舅母的身体是每况愈下。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所有老年人能得不能得的病得了一身,青光眼加白内障,高血压加冠心病,糖尿病加高血脂,最严重的竟然得了和她丈夫一样的病——食道癌。
大表哥过世后,大表哥家和二表哥家,算是打平了,谁也不用看谁的笑话了,即使当初二表哥过世后,二表嫂心里想着大表哥两口子看她的笑话,但心里总是不平衡的。现在终于达到了平衡。
但相对来说,大表哥家更惨些。因为二表哥家大闺女已经出嫁,儿子已经结婚,并且生了个孙子;小闺女虽然没有出嫁,但作为女儿,养几年,是不愁嫁的。大表哥大闺女已经出嫁,抱养的儿子,本身有点实在,大表哥两口子也不算是多有本身的人,娶老婆的事情八字还没有一撇,大表哥一不在,就剩下娘俩看不到头的苦熬了。
大表哥过世后,四个儿女就只剩下小闺女,本来想着让远嫁山西的小闺女养活舅母,哪里知道小闺女嫁的也是普通的家庭,小表姐和表姐夫整天需要上班养家,孩子不在身边。关键是舅母眼睛白内障加青光眼,基本上是瞎子,又比不得那些一直瞎的或者瞎的时间长的,能摸摸索索的自理,像舅母这样的,是一刻也离不开人的。
所以舅母在小表姐那里住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
两个表嫂商量,一轮半年养活舅母。
两个表哥不在了,但日子还得继续。两个表嫂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特别是大表嫂。虽然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但大表嫂为了儿子的未来,二表嫂也为了补贴儿子,都带着儿子或者跟着儿子出门打工挣钱。
于是,舅母就成了累赘。别的不说,就是每半年把舅母从一个打工的地方送到另一个打工的地方,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况且两个儿媳妇为以前的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不睦,让一个瞎眼的老太太夹在中间受气。
两个表嫂先是托人商量,后来面对面的商量,意思是舅母由一家养活,另一家出钱补贴。但怎么也商量不到一起:都愿意出钱,都不愿意养活。
而带着瞎眼的一身毛病的舅母打工,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变成了两个表嫂一轮半年在外打工,另一个在家里照顾舅母。两个表哥在世的时候,能压着两个表嫂,对他们的母亲好一点,起码在表面上能过得去。起码两个表哥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母亲好一些,毕竟,那是生养他们的亲妈呀。
现在让两个表嫂养舅母,基本上是指屁吹灯,是一点也指望不上。特别是二表嫂,更是为以前的她自己妄想的,舅母对她的种种不是和不公耿耿于怀,并且这种心理没有随着二表哥的去世削弱,反而加强了。大表哥的离世,对大表嫂打击很大,剩下孤儿寡母的,实在没有心情对舅母和颜悦色。
后来,两个表嫂终于统一意见,出钱,把舅母送进了养老院。
养老院估计实在不是像舅母这样一身毛病并且眼睛看不见的老年人呆的地方。呆了几个月,在舅母和养老院强烈要求下(舅母是感到生养了两个儿子,虽然儿子不在了,但养儿防老,住在养老院实在遮不住外人的眼;养老院是嫌弃舅母,两个表嫂出的那点钱,实在不能从中抠出点利润。况且舅母这个样子,随时都可能坏了,影响养老院的声誉)。
在舅母回去几个月后,终于走了。
纵观舅母的一生,不知道在娘家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嫁给舅舅,算是她父亲赌气所致。
嫁给不负责任的舅舅,就是苦难的开始,守着活寡,还得养育四个儿女,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舅舅去世,虽然心理上不再受气,但四个儿女需要养活,儿子需要娶亲闺女需要家人,事没少做心没少操。
等到儿女成家立业了,又迎来了延续几千年的婆媳矛盾,现社会又阴阳颠倒,婆媳移位,活得干气得受。
只有,随小闺女远嫁山西,大概是她这辈子的高光时刻,最舒心最不操心的时刻。谁知道老思想做崇,想过儿孙绕膝的幸福时光,得偿所愿,后来儿孙虽然绕膝了,但以牺牲幸福、也是唯一的幸福时光为代价。
接着就是正当年的儿女的一个个离世,估计,舅母对于自己的不幸已经麻木了。但儿女的离世更是她的不幸的雪上加霜的开始。
但开始也是结束,舅母在世上结束了,伴随着的,她的苦难也结束了。
假如有老天,假如老天有眼,你不能把所有想到想不到的苦难都往一个人身上堆吧?!
发布于 2024-10-27 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