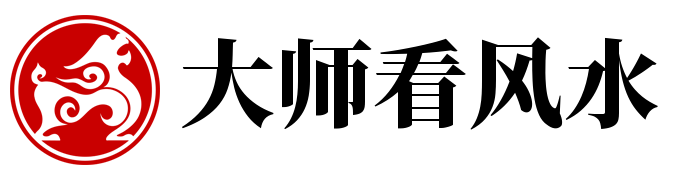黄宾虹书法:在文字和山水之间
黄宾虹草书临陆机《平复帖》
书法:在文字和山水之间
文-骆坚群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
探讨黄宾虹的书法,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孤立地评价其风格渊源及成就,总觉不妥;将他定位为“画家书法”,也会觉得不够。所以,我们不如把视点首先放在他的书法观上,即有关书法的理念,是如何与他的古文字研究相关联,他的古文字研究、笔法研究又与他的山水画是怎样的关系,以这样的角度和方法,或许可扪及黄宾虹艺术世界的灵魂或谓根基,由此再来看他的书法实践,方可有所依据。
首先,我们不把黄宾虹定位为书法家,毕竟他终以山水画大师名世,而且,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典型,即一生修炼,暮年方得成果。虽然,一个画家,尤其开一代风气的宗师,他的选择,他的成就路径,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本人的资质天赋,画史发展本身的规律,所身处的历史机缘,都在深刻影响、规导着他;但是,在大致把握艺术史的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先将着眼点放在黄宾虹之所以能成大器的“慧根”是什么这一探问上。也就是说,在他的资质天赋中,什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慧根”,且这一“慧根”与其大器晚成之“器”又有着何种关系。
黄宾虹大篆七言联
有这样两条线索应该很重要,一是黄宾虹在近 60岁时编定的《黄氏先德录》中,记下他8岁时与族中前辈翰林公黄崇惺的一段交往:小小年纪即用“六书象形”的原理来回答老翰林“何为蚱蜢舟”的问题,博得老翰林的惊奇和褒奖;二是在78岁时将编订了近30年的著作《古印文字证》交付刊印时作诗《识字一首》,颇为自得地回忆起“曩余秉庭诏,爪掌识会意。赐赍襁负中,嬉笑得饼饵”的童年趣事。
我们知道,60岁前后起,正是黄宾虹于山水画真正开始了殚精竭虑的“变法”探索进程;80岁前后,则是他开始走向功德圆满之时,在那样的时刻里,他自己是否也在有意无意间寻找、印证那种或可称之为“慧根”的东西呢?于“六书”即汉文字的造字法则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别颖悟,应该就是“慧根”之所在,黄宾虹自己强调这一点,当有深意在焉。
黄宾虹草书《千字文》
黄宾虹的深意关乎画史在近代的进展,“道、咸金石学盛,画学中兴”,即金石学是中国画经靡弱之后有望复兴的重要学术背景和学术动力,这是黄宾虹提出并不断完善的重要见解。而金石学也是他最早开始并持续一生的研究课题,他庆幸自己有这份特别的天赋和机缘。黄宾虹最早的著述是《叙摹印》,最早的著作是1903年编订的《宾虹集印》。1907年出徽州初到上海这个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时,识其画者寥寥,但都服膺其为藏印大家,是释读古文字的专门家。我们今天读到的他与友朋们的信札往还中,最多见的还是有关所藏古印或过 手古印的通报、印蜕的互递、印文的商榷等。
从1903年始,一生编订所藏古印谱在六七种以上,而最自矜的是所藏大都为六国古玺,下功夫也最深。因为在他看来,六国时期,上承三代,下启秦汉,南北东西各地域的文字,无论字型构造的空间关系还是线条形态,都呈现出自由烂漫、变异多端的特征,最具开放意味的创造性。 从1911年开始,他搜罗、排比有文字的陶器残片、封泥、陶范及与之相合的古玺。至1929年,运用刚刚进入中国的考古学和考古方法,编成一册《陶玺文字合证》,影印陶、金两组文物,相互印证“昔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的史实,也“可证实印之用途”。“说略”中还称,于此古玺文字可见出书体及风格异态:“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是以为书法源流之参考”。
黄宾虹行草高启诗《仪秦》
进入晚年的黄宾虹对有意为其集画成册印行出版的朋友表示,他有心出版期望流布于世的,一是他的画史研究著述,二是“发人所未发”的古玺及自己对古玺的释读。及至92岁逝世后,其夫人宋若婴携子女捐给国家的遗物中,古印已积有893方,手订的大小官印、玉印、图腾等印蜕并附释文共6册,是他一生心血所聚。
《黄宾虹常用印集》等
以这样的研究经历和成就,来印证古已有之的“书画同源”说,不会是空泛的。被文化圈内称为“当世能文识字人”的黄宾虹,释解古器物中的文字,也是为证经、证史、证文字源流,《陶玺文字合证》即是以一种更可靠的材料和方法来寻证史实。只是不同于一般文字学家、印学家,最终以绘画名世的黄宾虹,不仅更注意文字、书体、书写者性情与书法乃至绘画间的关系,更注重“六书”中“象形”一法,试图从考古发现中寻获上古三代“书画往往难以分别”的更多证据,从而对“书画同源”说提出自己独到的发现和见解。
在给弟子刘作筹的信中,谓“甲骨殷契及钟鼎古文中,图腾一类,有字有画,画在古文之先,为最近考古学家所公认”。 在四川游历时,得一“巴蜀王”古印,黄宾虹考为东周时物,尤贵其文是“书画未分之证”。这种类同图画的符识当是六书“象形”之滥觞。黄宾虹将三代铜器中之纹饰,甚至“夏玉”即良渚、龙山等文化遗存中的刻划符号,亦看作是文字的雏形。以画家的眼光和立场,他所看重的应该还有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最初始的“空间 观”。黄宾虹在北平时,给张海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方今议造新文字(简化字)者,形声似当并重,而形尤为中国古文特采,民族精神,胥在乎此。专门学者,更当珍宝,恒亟亟于传古,尚希同志奋起加意,为周秦诸子学术竞美希腊、拉丁、埃及之上,永不磨灭。”
黄宾虹草书临孙过庭《书谱》
在给弟子刘作筹的信中也明白地写到:“中国文字重在象形,与外国拼音并重。”将这种中国古纹饰、古文字之形的拈出,尤亟称为“民族精神”之所在,是画家黄宾虹独到的立场和视野。尽管黄宾虹没有用“空间观念”这个词,但外来艺术所显示的异样的空间观念,已空前突兀地出现在国人面前,自小就是摹写高手的黄宾虹,必然会有一个善于辨别物形以及作为符号的文字之形的心理和眼睛,加之敏感、深邃的文化人的哲思,自觉不自觉地来思考“空间观”、“艺术语言类型”这样的问题。虽然唐张彦远、元赵孟頫早有“书画同源”说的提出和论说,但黄宾虹正值时代转换之际,所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当然也有机遇,如考古学及考古新发现。
由“识字”即古文字的研究,以证实“书画同源”,这于近代画史是重要的,它证明了中国画的语言方式的正当性,以及延续并光大这种空间理念的艺术的必要和必然性;这于黄宾虹也是重要的,他正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打通了从自然物形到文字之间、从文字到山水之间的通道。对此,他有一段极生动的叙述:
“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凡山,其力无不下压,而气莫不上宣,故《说文》曰:’山,宣也。’吾以此为字之努;笔欲下而气转上,故能无垂不缩。凡水,虽黄河从天而下,其流百曲,其势莫不准于平,故《说文》曰:’水,准也。’吾以此字为勒,运笔欲圆,而出笔欲平,故能逆入平出。”
黄宾虹行草宋讷诗《壬子秋过故宫》
这是以对自然生命的感受和理解来动态地观照汉字的空间构成以及书写过程即书法的本原精神,此正所谓 “道法自然”。同时可以想见的是,黄宾虹如何构筑起自己内心的空间依据和书法法则。接下来是如何“以字作画”:“凡画山,山中必有隐者,或相语,或独哦,欲其声之可闻而不可闻也,故吾以六书会意之法行之;凡画山,山中必有屋,屋中必有人,欲其不可见而可见也,故吾以六书象形之法行之;凡画山,不必真似山,凡画水,不必真似水,欲其察而可知,视而见意也,故吾以六书指事之法行之。”
尚有观群山形势,可悟文字书法的布白当“不齐而齐”;画山之转折须以怀素草书的“折釵股”为之,山之阴阳向背则以蔡中郎的八分飞白;山之屋、桥欲“体正意贞”用颜鲁公的“锥画沙”,远树及点苔则是“印印泥”法;而流云不滞以钟鼎大篆法,水波畅达以小篆法。这段夫子之道,差不多就是他的全部秘密。书画同源,于黄宾虹不仅仅是理念,他的山水画,他的书法,尤其大篆书,法归于道,道归于一,只须读懂他的这段话,所谓黄宾虹艺术世界的灵魂,庶几已可扪及。
黄宾虹篆书七言联
进入暮年的黄宾虹,大约80岁起,开始不断写一些“自叙”“自传”类的文字。在他的遗物中有不少这样完残不一的手稿,开篇所记的总有这么一段往事:幼年六七岁时,邻舍有一老画师倪翁,黄“叩请以画法,答曰:当如作字,笔笔宜分明,方不至为画匠。再叩以作书法,故难之,强而后可。闻其议论,明昧参半”。 敏于“六书”的黄宾虹,小小年纪里,同时还深藏着一个“明昧参半”的有关书法及书法与绘画关系的难题思考。这一思考,不也是其“慧根”之一隅吗?
倪翁所谓“笔笔宜分明”的“作字法”或曰“作书法”,应该是指“作字”即构筑的这个空间,要“分明”、要合理,但他的重点也许是在构筑即“写”的过程中,如何笔笔灵动地写,有势有韵地写,以求遒美感人。“六书”作为造字法则,保证了汉文字视觉空间的合理完满,那么笔笔灵动而遒美的法则和保证是什么呢?是笔法。黄宾虹总是不忘幼年的困惑,是因为破解与“书画同源”相偕的命题“笔法相通”,也用了他一 生的精力。也所以,一生精研“用笔”、“笔法”,黄宾虹却不曾单以“书法”为题做过一篇专论,但“画法全从书法中来”,是他最坚定的信念之一。秉此信念,1935年,在所撰《画法要旨》中有“五字笔法”的提出,当是最重要的成果。
黄宾虹行草高启诗《姑苏杂咏·范蠡》
黄宾虹借重金石学学术背景,当然也看到了金石学给书法和绘画带来了从结体到笔意的批判意识和“解放”意识,结果是风格更趋多样化,而笔线的形态则将更加无法规定。在这样的现实与前景面前,一种再次明确“法理”的要求产生了。黄宾虹的“五字笔法”,即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回应。“五字笔法”的提出和论说有一个过程,前后有多篇著述论及,这里简述如下:
笔法一为“平”,如锥画沙,起讫分明;亦如水,天地间至平者为水,纵然波涛汹涌,终归于至平之性;用笔翻腾使转,终根于平实。
笔法二为“留”,如屋漏痕,积点而成线,笔意贵留,线条沉着而质厚。南唐李后主“金错刀法”与元鲜于枢悟笔法于车行泥淖,皆为“留”法解。
笔法三为“圆”,如“折钗股”,如“莼菜条”,连绵盘旋,纯任自然。董、巨披麻皴用笔圆笔中锋,圆融无碍而绝去圭角。
笔法四为“重”,如枯藤,如坠石,也如金之重有其柔、铁之重有其秀。能举重若轻,是力能胜之,如米元晖;化重为轻,则气胜于力,如倪云林。
笔法五为“变”,转换不滞,顺逆兼施是变,得古人法而超出古法之外也是变。
黄宾虹篆书七言诗
也许谁也不会感到新鲜,历代书论中,这五个字及“锥画沙”“屋漏痕”等比附早已耳熟能详。但传统笔法的论述往往从执笔、运笔到结字体势、用笔使转等面面俱到,法理与具体的技法及线条效果混为一谈。虽技法及效果从法理来,但容易造成技法即法理的误会。而在一法理之下可以有多种技法及线条效果,即如黄宾虹论“重”时谈到的“米元晖之力能扛鼎者,重也;倪云林之如不着纸,亦未为轻”。可知,法之理者,不再是某个正确的执笔姿态,不是点画的起落笔的种种规矩,而是这一切技法的依据。这一依据,来自自然理趣,来 自“名古人”的实践结晶。我们看重黄宾虹的这一理论贡献,不仅是因为他对历代笔法论说删繁就简,摄其精诣归纳出一个高于技法的法理概念,还在于他将诸笔法皆指向了合乎自然理趣而生生万变的“力”即“线条质量”这一命题,不仅以此统摄和超越了以往的笔法论说,也不容置疑地证明了书法和绘画相通在用笔笔法,其归于一的仍在线条质量。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黄宾虹证明“书画同源”与证明“笔法相通”是内在关联和顺延的。这其中,汉字的空间理念与书写即笔法的重申,不但是为揭示中国艺术精神的本原性,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挑战和机缘面前,五字笔法还重申了它的开放性。黄宾虹所论述的第五字“变”法中,山水木石,参差离合,抉其内美,存于天地的自然法则,是变的依据和不竭之源;书体衍变、柔毫性能、心宜手应,是从笔性的角度,揭示了心手合一开无穷样式的可能性。用自然之理、笔性之理到心性之理来证明“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而证明“超出古人之法”,传统得以延续、嬗变的原因和必然。这是黄宾虹在金石学背景下,对近两千年以来的笔法论说,作了一个举重若轻的提升,或者说是又一次厘清。
黄宾虹篆书七言联
至此,我们似乎也有了端详解读黄宾虹书作的准备了。以今人的“创作”概念,黄宾虹确实较少“创作” 意味的作品。以今论者所关注的大篆、行草、题跋、简札等书作观之,似乎唯有大篆书因大都为应人邀约而作的篆联,似最具作品意识,也最早受人赞赏。余绍宋在1929年、1935年两次收到黄宾虹所赠篆联,也两次致函表达激赏:“所论籀篆笔法递变各端,诚为不刊。今人作大篆,往往用小篆笔法,或杂用草隶体势,皆由未明此理。故绍宋尝推先生所书金文并世无两;岂唯并世,自明以来所鲜见。”余绍宋说到了点子上,新考古学尚未发明前,人们未能厘清甲骨文字与秦小篆之间有商周三代及先秦六国文字也即金文或称大篆古籀,将秦小篆及秦汉间草隶与三代六国古籀大篆混为一谈。黄宾虹于三代金文如孟鼎、 钟多有研习,尤精先秦六国古玺文字的考订及肖形“图腾”研究,能明了“籀篆笔法递变各端”,并用以书篆联等,自然能“并世无两”“自明以来所鲜见”。
黄宾虹 篆书五言联
其中1929年所赠篆联已由余绍宋后人捐入浙江省博物馆,与黄宾虹后人所捐5000余件书画作品相伴,亦因缘也。其时黄宾虹66岁,尚在上海,与早年略嫌稚弱的大篆书相比,笔致清和通简趋于成熟,也与当时的山水画同一旨趣。十年后,赴北平居又十年。从北平十年间的画稿、书稿(大量照录古人书迹)看,金石笔意的研习才真正成为他主要的案头功课。但无论是早期的稚弱,中期的清简以至晚年的老健浑融,都与当时常见的雄强霸蛮风和矫饰安排的装饰味大异其趣,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回到本初的努力,是为体味、揣摩上古三代先秦六国时人“图画象形,书画未分”时“未知有法而法在其中”的那一种空间姿态,体会书与画“日久渐分”后“参差离合,妙合自然”仍能自主率真的书写。所以,在他的篆联里,我们可看到他在行笔过程中那若即若离的提按、留驻,尤其些微的波折、颤动,最具生命律动的意味,而每一笔的交接、转折与中、侧锋的随遇而变,既是他大篆书风的特征,也为他的绘画用笔开同一法门。
大篆书的用笔甚至结体都可视为他绘画用笔的“密码”,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将他似从画笔短皴脱颖而出的行草款书视为一种“画家字”。宋元以后,即书法入画以至书、画同法后,画法也会反过来影响书法, “画家字”必然出现。可见,只有境界和功力的问题。黄宾虹的题跋简札尤其晚年所书,非但与其画笔别无二致,更与他90高龄的人生一样苍苍茫茫、风神款款,最受敬重。
黄宾虹行草王十朋诗《武王》
尽管题跋简札也是最古老的作品品类,但今天人们更关注长卷大轴,黄宾虹其实也做过这样的努力。只是大都是习作,即未发表未持赠友朋的积稿,而且无款无印,相当部分是或临或录古人书迹的练习稿。北平期间,即80岁前后,在给朋友陈柱尊的信中告以日课为:“每日趁早晨用粗麻纸练习笔力,作草以求舒和之致,运之画中,已二十年未间断之,但成篇幅完毕者罕见。”这段话解释了这批草书积稿的来历以及作草书的目的,是为练腕力,为涵养“舒和之致”,为“运之于画”。
黄宾虹篆书七言联
确实,在他以“黑密厚重”著称的山水画里,若无这种“作草” 之功的长年积累,如何能从密实中见出虚灵通透,而在他晚年甚是自矜的“简笔画”里,那些倏忽几笔但极为得手的线条,如神龙出没,背后必然是这“作草”之功的支撑。在这类“作草”积稿中,大都照临明人如祝允明、 陈道复、王铎等,也有相当部分融入汉隶和章草笔意,所论笔法的文章和信札中,也总推崇“隶意”。“隶意” 的注重,从技法层面看,或是为草书尤其明人草书过于圆熟流变可能有亏古质而作的一种弥补和强调。行草书擅 “变”而生文,篆、隶书特具“平、留、圆、重”有其质,楷隶之间的章草皆有文、质,文质彬彬是为君子。黄宾虹二十年日日所求的“舒和之致”,必集古籀、篆隶、章草、行草于每日的孜孜挥写中涵泳而来。其功夫意境当非但“运之画中”,也必定渗透在行草款跋之中。只是在那些纯为书法创作的草书卷轴,在现今书家中却有相当多的看法是,其草书笔法尚未周全,认为或可能是因为书法尤其草书笔法与绘画用笔终有径庭之别,适用于山水画勾勒的籀篆用笔抑制了他的草书用笔,所以他的草书点画有生涩缺落之撼。
黄宾虹行草文明诗《西苑·琼花岛》
或者,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草书在明人,即从祝允明到王铎以后一直低潮,黄宾虹同时辈中也仅有于右任在努力再造时势,而正是黄宾虹时有生涩缺落的“草法”引领了一代草圣林散之,然而在林散之风卷云舒的草法里,为何总能隐约扪及黄宾虹的“生涩缺落”呢?这真的是个问题。是为进一步先退三步吗?是为重建先解构吗?因为草法的点画于黄宾虹真的是个难题吗?
讨论黄宾虹书法,需从远古的“图画象形”到文字肇始,再到可为绘画之法的书法,这样的书法太不单纯了。说清黄宾虹书法不容易,说清黄宾虹与林散之间的传承关系更不容易。但,引人入胜,值得继续探讨。
黄宾虹行书王蒙诗《竹趣图》
发布于 2024-10-19 08:27微信分享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