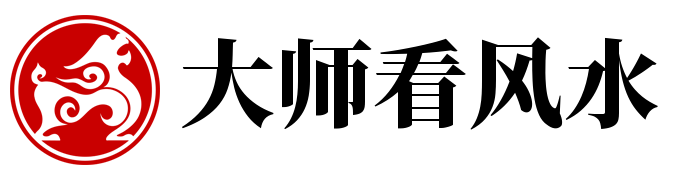知命识相五十年
男人大贵相鼻颧是关键
“得富贵相则富贵,得贫贱相则贫贱”这是汉代鸿儒王充在其名著论衡命义篇的一句名言。
孔子学生夏曾说过“富贵在天”的话,这所谓在天,当然是指非人力之所能勉强的命相说的:因为命相之事是生来就注定了的。
虽然时至今日男女平权,富贵之事应无男女之别,但在命相上仍有极大不同之处。举一个明显的例说,不论男女,鼻总是五官中最主要。但男人若得“削鼻如刀”的相,只是为人“苛刻”而已,而女人得此相的,性情即未必苛刻,而“剋夫”的不幸总是难免的。又,男子颧高的只是表示有“权柄”,而女子颧高的,除喜欢弄权之外,也常有剋夫之嫌。
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成功之时,孙中山先生还在欧洲,因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当时就以武昌为革命军中央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出示安民。这是阴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阳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事。到阴曆九月初九,清帝宣统下诏罪己,十一日以袁世凯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二日颁布君主立宪的宪法:十六日下令释放行刺摄政王的汪精卫,这一连串惊天动地的事,使全国震惊倒不算奇,而惊动当时北京的命相界以及相信命相的人,街头巷尾谈的并不是以政治改革为主题,而是以汪精卫命不当死,袁世凯相有大贵为话题。
因为当去年二月汪精卫谋炸摄政王事败被捕之后不久,北京就盛传摄政王因见汪精卫的仪表可爱不愿杀他了;又说摄政王叫看相的去看汪精卫的相,说他将来将是南方帝王,所以要想用他了;而到此时汪精卫竟然获赦了,岂不可怪!至于袁世凯,老早就被北京算命和看相的拿去做广告,说他的大贵将不止于北洋大臣的高官,而今也果然是君主立宪汉人的第一任的内阁总理大臣了。
更奇怪的,因为袁世凯相信命理更相信看相,于是他派人四出去找中山先生和黎元洪的八字。中山先生的八字虽然一时找不到,而黎元洪的八字却找到了,为要命相合参,他就派一位善观气色的曹先生和当时闻名全国的相士钓金鳌的老师韩先生,到武昌去设法看看黎元洪的相貌和当时的气色,不久,他们两人就秘密地到了武昌。
韩曹两位先生到了武昌,就住在韩先生的另一个高足在武昌长街挂牌开馆以善观气色闻名的赛金鳌的家裡,因为他们两位都会抽鸦片,住在旅馆不方便,住在徒弟家裡当然舒服得多。刚好,当时黎元洪都督府裡有一个罗科长是赛金鳌的朋友,也是黎元洪的亲信,在八月初时曾被邀去看黎元洪的相。当然不是黎元洪要他去看相,而是这位罗科长知道黎元洪将有起义之事,他本人相信命相,就乘著一天私人的宴会,叫赛金鳌作一个来宾,寻机会去看看黎的气色如何。
起义之事当然罗科长不会告诉赛金鳌,只告诉他说,因清廷要改制,当时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要黎氏进京面商要公,看看黎此去以后官运如何。赛金鳌把黎氏看了之后对罗科长说,黎氏驿马并没有动,看来进京之事不成,这话把罗科长说得心服了;于是就问:“那末此后官运有无更动昵?”赛金鳌说:“在二十天之内他将有陞迁之喜,而且叱垞风云,名闻天下。”第二天罗科长把这话告诉黎氏,黎氏本是相信命运之事的,他自幼就听见自己出生周年那天,和尚登门看相的故事,和尚曾在三个婴孩中指他说:“此儿头平额润天仓满,将来出将入相,贵临极品无疑”的话,所以一听见罗科长的报告,就微笑地说 :你再去问他,看我此后是否应当“弃武就文?”“弃武就文?”罗科长说:“当今不是太平的世代,弃武就叉百什麽好处?”黎氏笑道:“你不是也知道和尚曾说我将来耍‘贵临极品’吗?那末,像今日的徐世昌一样,当一个内阁协理大臣,岂不就是‘贵临极品’?”原来黎元洪的父亲和他自己,一向都认定和尚所说的“出将入相,贵临极品”就是宰相,也就是君主立宪的内阁总理大臣,黎氏心想,革命成功之后,他当一个内阁总理也心满意足了。
当日罗科长就跑去问赛金鳌。当晚向黎元洪回报说:赛金鳌说你五个月之后才能弃武就文;惟是,从此位高于权,逍遥自在。黎氏听了就用怀疑的口气说:内阁总理大臣。像日本的伊藤博文等,都是位高权重,何谓位高于权?你再去问他,这话到底怎麽解释?好笑得很,赛金鳌只能就相上看出位高于权,而不能作出切实的解释。所谓位高于权,就相貌上看就是鼻胜于颧;但就当时的情形看,虽然前四个月清廷已颁布内阁官制,以皇族中人奕劻为总理大臣,以皇族那桐、汉人徐世昌分任协助大臣,这徐世昌的地位就算是位高于权,名义好听,而实权没有;然而赛金鳌因远在湖北,也不大懂政冶上的官职和权力,所以一时无法解释。
好在他替黎元洪看相后不到半个月,武昌果然起义成功,黎氏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的都督,总算他已把黎氏的大事看准了。
武昌起义是阴曆八月十九日,而袁世凯派赛金鳌的老师韩先生来武昌,大约是十月初,那时候武昌成立中央军政府,黎元洪正预算等待中山先生返国决定挥戈北伐的。所以黎元洪又叫罗科长来请赛金鳌去看看气色,在这两三个月之内,是否有掸戈北指的可能;因为前次八月初赛金鳌初次替黎氏看相时,曾说黎氏北上不成,所以现在想要他再看看气色有无转变。赛金鳌去看却看不出黎氏有挥兵北伐的气色。
但黎元洪对赛金鳌说,革命军政府已经成立,有进无退,没有不北伐之理,只待下月孙先生返国,就要下令北伐了。赛金鳌听了,不敢再说下去,只说且等下月再来看看气色有无新的变化,就退出来了。正在此时,老师韩先生突然来临武昌,赛金鳌真是喜出意外,他正想把对黎氏相上的两个疑题向老师请教:一个是位高于权的问题;另一个是北伐气色的问题。
韩曹两位先生听见赛金鳌已和黎元洪有此接触,也算喜出望外,第二天就由赛金鳌设宴为老师洗麈,邀请罗科长作陪,一面请罗科长转呈黎都督,说是赛金鳖的老师来到武昌,想要进见都督瞻仰威仪。黎氏当然同意,第三天就由罗科长和赛金鳖伴同韩曹两位,进见黎氏于武昌军政府的内客厅了。
韩先生拜谒黎氏之后,就对黎氏作如下四点的简单新语:第一、说黎氏从此弃武就文,不再掌握军符;第二、三十天之内,黎氏的驿马乃向东走,不是北上;第三、在这五年之内,位高于权,即就地位言,比内阁总理更高,但没有实权;第四、第五年起,将是际遇风云,权位并隆之时。当时黎氏为著保持军政府首脑的庄严,并无问话,只是微笑颔首而已。
赛金鳌的老师进见黎元洪,在黎氏本人和罗科长以及赛金鳖他们几人看来,以为这是难得的机会,韩先生能以垂老之年由北京来此替他看相,而内裡他们却不知韩曹二人正合下怀,替袁世凯做了一件大事看到了黎元洪的相貌,韩曹两位即乘坐京汉铁路火车,回到北京,就对袁世凯报告说,依照黎元洪的气色论,在最近三个月内绝无北上之理,但此人有磅礡忠厚之气,前途无量,宜与为友,不宜为仇。至于革命军是否乘胜挥戈北指,这问题似乎不在黎氏身上,而在正在欧洲回国途中的孙文身上。
此时袁世凯已得知孙中山先生将于十一月初抵沪,并已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于是另派南京上海有熟人的人三位,陪同韩曹二位赶去上海,要看看中山先生的相貌,是否有一朝天子之相;因为当袁世凯奉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这位钓金鳌老师韩先生原係袁氏的熟人,他曾说袁氏从此将有登极称帝之望;当时袁氏曾笑道:这是皇上叫我出来收拾残局,准备和南方革命军和议的,我那有此种妄想。韩先生说:就北方诸位大人和相貌来说,承继大统的只有我公一人,至于孙文的相貌如何,虽然没有看见过,但可以断言的,孙文纵然也有帝王之相,也只能统治南方,成为南北割据局面,绝不能取我公而代之;因我公此时正行一生最佳的运,非任何人所能夺取的。
但是袁世凯的内裡雄心万丈,他不甘与南方割据局面,他想统一南北,如果清廷大统不绝,实行君主立宪,他想做一辈子的总理大臣,独揽大权;如果清廷失败,他想利用南北和议的机会,要做新中国的首任大总统;所以他一定要韩先生去看看中山先生的相貌,是否与他有南北分庭抗礼的气宇,作为他考虑南北和议决策的一个主要问题。
中山先生是十一月初六日到上海,韩曹二位虽然也赶到码头冒充欢迎人众,但看不见孙先生。初十即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南方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过了三天,即一九一二(壬子)年一月一日,国父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时,韩曹二位才有机会夹在会众中,看了孙先生一面。当时二人同声讚叹:异人,异人。
本来袁世凯是派三个对南京上海熟识的人陪同韩曹两人来的,那天就由一位姓秦的陪同入会场。当韩曹二人走过中山先生面前,看到临时大总统就职后的威仪时,两人的连声讚叹“异人,异人”时,那位姓秦的吓了一跳,以为中山先生真是一朝天子之相,袁世凯的局面不会久了。因为姓秦的也略知相术,一回到旅馆,不待韩曹先开口,自己就说:这位孙大总统,我看他的相貌,既不魁梧,也不清秀,我们北京每一个部大臣都比他像样,他竟然当起大总统,这真是人奇异了!这还不算奇异,此人还有更奇异的在后面哩!韩先生说:他敢于把三百年的清廷推翻,原来确有异相。还有什麽更奇异?难道他真是一朝天子不成?姓秦的表示十分怀疑。
你不必为咱们的袁大臣天下担忧,他不会夺取袁大臣的天下的!曹先生看出姓秦的有此不安心情,就如此告慰他。
韩先生又接著说:从前郭子仪的儿子曾对昇平公主夸言“我父薄天子而不为”,今天我看到孙文的相,他才真正是一个薄天子而不为之人了!
薄天子而不为?那末他今天为什历就职?姓秦的表示异议。
那是另一回事。你看吧,不久他就会不干的!韩曹二人逗留南京期间,果然看见黎元洪也来到南京,证实他月前对黎氏说过三十天之内,要向东行,不是北上的断言。一月一日中山先生就职,一月三日,各省代表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从此黎氏任副总统,直至民国五年,袁氏去世始接任大总统职位,这又证实了赛金鳌对黎氏所说的前半段所谓位高于权的事实;因为当时赛金鳌和他的老师,都还不知未来的政制有一个职位高于内阁总理,而权力不如内阁总理的副总统。这是关係命相先生的智识问题。
袁世凯在北京,知道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心中甚为忧虑,以为革命政府既然成立,而这位久为清廷认为“大寇”,亦为民间认为“大炮”的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就情势上看,南北和议的计划是不会成功的了;就是成功,对于自己的终身内阁总理大臣,甚至大总统的美梦恐怕也做不成了。于是他满心急待韩曹一一人同来报告。
韩曹二人回到北京秘密地向袁世凯报告说:南京的革命军政府,虽然不会动兵北上,但中华民国的国号以及改元,已注定取代大清的大统了,看来,满清天下就要没落了。袁氏急问孙文此人到底是如何?韩先生翘大姆指称讚道:异人,异人;功盖天下名垂千古。曹先生在旁补充一句说: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
那末,据你两位看来,这大局已经定了吗?袁氏又质问韩先生说:以前你说我的命运又将作何解释呢?他们若既不会挥兵北上,我们那有把天下拱手授人之理?这其中自有很大的变化。
大清完结,中华民国成立,这大局是定了的;但就孙氏的相格看,他却不是富大总统的人,而且不久就要去职的。韩先生说了这话之后,袁氏听了大为错愕,就问:这到底怎麽意思呀!韩先生解释说:大贵之相以气宇为第一,我看孙氏的气宇,贵在帝王之上,所谓圣人的气局;是薄天子而不为的人物;所以他创立的中华民国是永垂千古之事。至于我所以说他不是当大总统的人,乃是就形象说的,他虽有高贵之鼻,而无丰满之颧,所以杝的权贵只限于临时大总统。是象徵开国之意,我看他的气色,这临时大总统在一百天之内就要辞职的。不过,此君乃中国的异人,望我公善与周旋,务须尊重,幸勿对他轻视!接著袁世凯就转头朝向客厅壁问的大镜子,看看自己的面孔,要韩曹二位说说他的鼻颧问题。当然,袁氏听了韩先生刚才说气局问题,已自知气局不如孙氏,就想在形象上争回自己的高贵。
于是韩曹二人就给他讲论关于大贵的鼻颧相格,首先就说袁氏的体型乃正宗的北人形象,而中山先生则是南人形象,其次说中山先生和袁氏的鼻,都是直冲天庭,极品贵格;而中山先生最特别的,就是两眉之间的印堂非常平坦广宽,为常人所难有,因此也只能看出是一个名高于位的人,能像钓金鳌的老师,韩先生看出“异人、圣人”的气局,而且断定他是个“薄天子而不为”的人,真太不容易了。
因为我们中国自古就是北方人的政治,统治中国的帝王都是北方人,而北方人的体格是魁梧高大,所以论体格以为魁梧是贵相,这是历史性的一个俗见,也是错误观念,后来又有所谓“北人南相”和“南人北相”为贵格说法。这种相格,多为富贵相,虽然是事实;但这不是最高贵的相格,因为人相的原则以纯为贵,以杂为贱;不论北人南相或南人北相,在原则上论,都属于杂,原属贱格的。其所以能贵必须杂而不混,即北相的就要一切像北人,南相的一切像南人,否则,若体型北相,性情南人;或脸型南相,体型北人,那就非贱为隶役不可了。
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和第一任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相型来说,两人的体型都是南人的纯和北人的纯,所以有此大贵。中山先生之所以能为国父千古,像韩先生那样能从气局上看出的,记得廿馀年前晤及钓金鳌和赛金鳌两师名垂兄弟,虽然他俩也能道出关于观气之法,但观察之术却不够工夫。
一般相者看中山先生只能道出印堂、鼻、眼和口四部位的优点,而不能看出其能功成身退和流芳百世的特点。钓金鳌告诉我,他的老师那次从南京到北京告诉他说:中山先生的气宇和形象的特点,在于气藏形潜。后来我从两个追随国父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中山先生的特点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动心。
至于鼻颧关係大贵的相,这还是就面貌上的部位说的,就大要上言,鼻的贵相,可用端正、不陷、平直、有力八字为断语。再高贵的,则是上接“宽坦的印堂”,下托“四字形方口”。
上面曾经说过,有鼻无颧也不兴,有力之鼻,也须要有力之颧为辅,左右两颧,以“不低、不敬、不露骨”三“不”为要领。看相看鼻不难,看颧倒是不容易。
陈炯熵明叛变时,中山先生返到上海。有一次他在法国公园散步,我的舅父和几个朋友也在那裡閒游。舅又一向在北京不认识中山先生,因为舅父会看相,同行朋友中有人认识的,就指孙先生问舅父:你看此人相貌如何?舅又一看,说:此君必是闻名天下的人。朋友再问:是否只有名气而无权位?答道:位显而不居,权藏而不用,非无权位也。这评语也可算是知相了。
女人剋夫相关係鼻眼颧
有一年在北平常与当时被号为彭神仙的彭涵芬君往还,不时也在中央公园的古柏树荫下品茶纳凉,閒谈世事,这位善观气色的彭先生,年青时原是一个看相先生,在上海新世界附近的西藏路路边摆过看相摊头,因为他有一天看准了一女佣人有性命之危,那女人果然投环自尽;而她的丈夫闻知却来找他要和他理论,他被迫无路可走,就跟著一个山东同乡在太古公司行船到英国去。后来就在英国半工半读变成一个留英的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当然不再重操旧业,就在故都政界中混,因为他比别人多一套善观气色,不久便大走其官运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五十多岁了,也是一个已当过财政上的局长要职。退守林下的时候,他虽然是个精于相术的人,但不喜欢替人看相;因为与人谈相常有困难,由于世人大都福相少,祸灾多;不直说,自己不愉快;直说,别人不愉快,何苦来?所以他经常是避免和人谈相的。但是由于他已经出名了,而熟的朋友又多,所以他几乎每日也都难免被邀请吃饭,或是别人上门要替人看看气色说几句的。
有一天我和他两人在中央公园裹正优悠地躺在籐椅子上面东拉西扯著。本来我若和他在一起,就难免时刻向他叨教关于相学上的问题的,那天我们决意不谈相理之事,只是一味清谈。
一会有几个游园的男女,正在我们的对面座位坐下。一共有五个人,两个青年男子,三位女人则是四十多岁的上流太太似的。因为坐得我们太近了,她们的一举一动又不能不引起我们多少注意,而我所注意的又不离本行,于是我和他又不能不谈到相的问题来了。
“你看这三位女人甚历是同格,甚麽是异格?”还是彭先生先开口问我。
我说:“一生足衣足食,不愁穷困是同格;夫、子、寿数则是异格。”
他微笑地又问:“请你说说她们的夫宫如何。”
“头上梳髻的那个‘夫贵’;穿背心的那个‘夫富’;著旗袍的那个‘剋夫’”
他又微笑地说:“你看的只是大体上不错,但其中颇有问题。”
他坐了起来,饮了两口茶。“那个夫贵不差;但那个夫富错了,不是夫富,是她自己富。还有一个同格你没有看出,她们都是‘剋夫’格,而且都已剋过了!”
因为当时我虽研究命相之学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但就这门奥妙的学问来说,还是初学,当然所知的还只属皮毛,所谓易知难精我自己是明白的,尤其是关于女人的剋夫相,有所谓“明相”和“暗相”,又有所谓“外五行”“内五行”和之别,而我当时所知的只是明相和外五行的一部份,至于暗相和内五行我就不识睇了。于是我听彭神仙这一说,就乘此机会向他请益了。
“她们三位都是剋夫格吗?我真不识看了!”我说:“那两位到底剋在在那裹呢?鼻也不削,颧也不高。”
“想你只知其一二,不知其三四,而且还有五六七八九哩!”彭先生说:“仅就明相说,女人剋夫,可分面貌、体型、和举动三方面,而初学的只知面相,现在你就以面相论,面相中,剋夫相关係于眼、鼻颧三部位。一般相士都只知女之鼻削、眼凶、颧高;三者为剋夫相,而不知有的情形并不如此。”说到这裹他问我,现在看的就这位著旗袍的剋夫女人,那明显的是所谓鼻樑削如刀;但那位穿背心的勀夫,却鼻樑下陷所致,至于那位头上梳髻的,虽然嫁夫必贵,而剋夫之相则繫乎眼了。
的确,我当时只知道女人鼻削、眼凶和颧高三种是勀夫相,而鼻樑扁平的虽知其係坏相,却不知道也是勀夫相,至于那个贵夫人的眼睛,我就完全看好,绝不会看作剋夫相的,后来经过他的解释,才知道女人眼眶大而露光的,在三十七八岁两年,就会剋夫的,不论男女,眼眶宽大原是好相,但若浮光不定,那又不好了。
据彭神仙的论断,鼻削如刀的女人,剋夫较早,在四十五岁以前,很可能不止剋一个,那位贵夫人当在三十七八岁两年丧夫无疑。最迟剋夫的是鼻樑陷下的,要在四十一岁后两三年内,但过此就不再剋了。
我们正在谈论之际,望见友人中医师刘幼雪大夫也带了几个男女同伴来游园,他原与彭涵芬也相熟,就过来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因为刘大夫是一个儒医,认识的病家很多,原来他也和对面座上的三位女人相熟,彼此也打了招呼,当时我就想,关于这三位女人的事,他一定知道的。
刘幼雪走了之后,与他家人一道来约有一位萧太太是他们亲戚,我也相熟的;于是我就问彭神仙:“刚刚和刘大夫太太圭在一起的那一位太太,你留意到了没有?”“留意到了,”彭涵芬说:“因为我们刚刚在谈论剋夫问题,所以我留意到了,你也认识她吗?”
“认识的,她是萧太太,是幼雪的表弟妇。”我又说:“你看她怎麽样?”彭涵芬说:“她已经剋了两个丈夫,而且都是死于非命。”
我说:“我知道幼雪的表弟,前几天因飞机失事死掉的,你说她以前还是以后还要剋一个?”
“我说的是以前还勀过一个,”他说:“看来现在她大概四十零岁了,我想应该劝她在四十七岁以前不要嫁人,否则还要勀。”
这位肃太太面孔长得并不恶,所嫌扚只是颧骨太高,所以戚友们都说她剋夫理由就在此,但我们初学的人只知道她会勀夫,又因为四十六七岁两年是走两颧,所以都以为要等到四十六七岁才剋夫,而不知不待走到两颧就要剋,而且以前已经剋过两个了。据彭神仙说,俗语有“一年嫁九婿,无婿过新年”这句话虽未免言之太过,但在严重剋夫相上说,却是事质。
他说他曾见过此种女人,就是鼻眼颧三部位如果都有剋夫相的话,她就不可能满一年而不剋夫,反而可能一年之内剋两个丈夫的。
过了几天我碰到刘幼雪,因为他知道我随时向彭神仙学看相,所以还不待我开口,他倒先问我那天和彭神仙在中央公园有甚麽心得没有?我就乘机问他那天坐于我对面座上的三个女人是谁。他就笑对我说:“你们看出了没有,她们都是勀夫的!”“是的吗?我只看出一个,而彭神仙晗把三个都看出了的。”“是的,那位韩次长的太太相貌很华贵,不是彭神仙不容易看出她曾剋夫的。”接著我就问到萧太太的问题。我说:“令戚萧先生前两年去世,我是知道的,萧太太的丈夫应当死于非命,你看怪不怪?”
“真的吗?他还有说她别的事没有?”
“他说她以前已剋过一个,也是死于非命。”
因为刘幼雪对于命理颇有研究,他听我说了就微笑道:“彭涵芬的相术的确比我们的命理高明。”
原来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被汽车撞死的。
鼻分善恶、贵贱、富贵三类型
无论男女,就面相说,五官之中,以鼻为主,鼻相可用上格和下格两种分划。属于上格的,又可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善相,即善人之相。乃指品格就的;第二类是贵相,即贵人之相,乃指权位说的;第三类是富相,即富人之相,乃指财富说的。
善人不一定富贵,但一生必定安乐和善终。贵人未必富,富人未必善;也都未必一生安乐善终。贵人之有益于人之事。当比富人更多;因为为富之人每自厚甚至不仁。
所以论福相,应以善为贵,贵次之,富为末。这是上格的三类,每一类又分为上、中、三等级,即大善、中善。小善;大贵、中贵、小贵:大富、中富、小富等各三级。
从前老钓金鳖在北京石看相时,初次花十块大洋请他清谈一次的,只能替人断定相局属于那一格和那一级而已,你欲细说,第二次再来。
普通看鼻相,善格之鼻以端正纯洁为主;贵格之鼻以通天有势为主;富格以丰满藏孔为主。这也只是粗浅大略的看法,不够精到,也不能断定其属于上中下的那一级。
要断定其为大贵、中贵或小贵之类,就必须与其他五官和全局看了。
从前北京有个精于相术的秦四爷,据说他曾在上海看见过国父中山先生,他说中山先生的鼻是人善兼大贵,但无富。
他也看见过上海大富翁哈同。他说哈同的鼻是大富,小善而无贵,所以据他说,大善兼大贵鼻有,大贵兼大富之鼻也有;大善兼大富之鼻就没有;而大善,大贵和大富三者兼全的便永远没有此种人了。
至于下格的鼻相,也分为恶、贱、贫三类,每类也分上中下三等级。三类中以恶相为最劣,因为必然他自己不得善终,死于非命,甚至全家惨死的。恶相不一定兼贫相,贫相也不一定兼贱相,不过,由于社会制度的关係,贫相的最多,贫兼贱的次之,而恶相的则最少。
所以所谓世上恶人多并非事实,而贫贱的人多,倒是事实。由于贫的人既多了,因贫贱而暂时作恶的自难免,因而使觉得恶人多了。其实,这并非固定的相格,而只是暂时的变相。这也就是所谓相由心改的理由。
虽然男女的面相都以鼻为主,而男女的鼻却也有分别,并不能同样看法的。同样的鼻,放在男人面上是贵,放在女人面上不一定是好,甚至是坏。
鼻的三种型,惟有贵型不能男女同视,其他善型和富型两种,男女都可以同样看法。也惟有贵型的鼻,必需要以颧相配,如果无颧相配,可能反贵为贱。
至于富型的鼻,如不得相配的颧,至多不能大富或富而不久,不致于反富为贫。
再如善型的鼻,则与颧相配与否无关,绝不至反善为恶。这是鼻三型的各具其不同的特质,学看相的人需要明白的。
就贵型的鼻论,蒋总统的鼻便是大贵之鼻的典型。我相信,凡是见过蒋总统的人对其尊容所最能触目,同时一闭目就能得其印象,他的五官就是鼻与眼睛最特别,贵型的鼻第一就是正直,第二是樑高,(即两目之间的鼻樑,相书上叫做山根的不陷,能高起与两眉之间的印堂连在一起)。第三是有力,即不宜有肉亦不宜露骨。蒋总统的鼻,就是合此三个条件。
故国府主席林森的鼻,正直够,但山根不够起,也不够有力,他只是中贵兼大善的鼻,就鼻的全局论,蒋总统的鼻则是大贵兼中善和中富的鼻,所以虽贵为元首,而一生难免劳碌奔波,就安逸言,反而不如林主席了。
至于蒋夫人的尊容,最使人得到印象的,则是左右两颧的丰腴与秀美的鼻型。从前有不少的人初看蒋夫人的颧,都以为有颧高不利夫星之嫌,或以为她是相当厉害而好弄权的夫人。其实这都是皮毛之见,蒋夫人的颧可以列为善型兼贵型之类。何以是善型昵?可用丰、润、圆三字来说明;何以是贵型呢?可用不突兀、不露骨和不见柄‘三不’去说明。因此,蒋夫人的才能,全为相夫之用,而不自用。
北京老钓金鳌和秦四爷两人,都见过慈禧太后。他说,慈禧太后的颧就是突兀露骨和见柄;所以好在她的鼻不贵,否则,何止垂帘听政而已,弑帝自立,早已是亡清的女皇帝了。
看相以看鼻为主;因为它具备了善、贵、富三型的基本而且玄妙的条件,不特可以看一个人的前途,更重要是可以看人的善恶。
与命抗衡的事例
一般算命看相先生每每为著掩护自己判断的正确,对某一件事常常向人强调不可避免,或必会发生的说法。此种坚定的态度,确定的语气,原是好的。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命理也不能免。比如断定一个人的寿数,命相先生每每说某年坐铁轿子也抬不过去之类的话,而事实上到了那年那人并没有坐铁轿子也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这不是叫人最少空怕了几年吗?
关于断定寿数一事,有的就命相上看很明显的,可以把它作一个铁定的判断,但最少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不容易判断的。就是很明显的,可以作铁定的断语的,也可能有例外。
这可能由于八字本身的变格,或因行善积德的影嚮,也可能由于本人绝对谨慎的结果,固然这事种例的百分比佔得很少,但必须保留这些例外。
除属于变格不能说其理由外,属于积德的事例倒也不少,如有名的唐朝宰相裴度,年青时有一天路上碰著一个相士,说他将来要饿死;过了若干年,裴度又碰到那相士,竟因行善改相,变为前程无量的好相。
有个现在还在世的老算命先生,他算自己六十岁那年恐怕度不过去,就避到镇江的焦山,在长江的江中孤岛上住了两年,竟然也安然没有死。
我有个老友刘君,北洋政府时代在北京做事,算命的说他命中有一妻两妾;在当时的北京风气,男子娶妾是很平常的,有地位有钱的人,不必命中有妾才娶妻,髮妻也不一定要反对的。但因这位刘先生,他平常已经反对娶妾,有意与命运抗衡,偏不娶,后来生了三个孩子都夭折了,算命的说他妻不留子,妾才能留子。亲戚朋友们也都劝他纳妾,但他偏不纳。
结果,五十多岁他的太太又生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终然把命运的支配也硬改过来了。
这类事例固然不多,但我们必须承认有此事实。不过,要注意的这裹有行善与作恶的分别,命中有妾而不娶妾是行善;若命中无妾而要娶妾,或因自己享受而娶妾,那便是作恶了。属于行善之事,反抗命运可能成功;因为这正大光明,于心无愧之事,便是造化命运的动力。
如果为看作恶而去反抗命运,那便非失败不可的。此种属于行为心理作用,本身就是命运的动力,万不可忽视的。
算命看相各有所长
中国看相之术,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朝就已精到了,一直到现在,由于人们把它作糊口之计,江湖之技,所以大有一代不如一代,反而退步到不如早年的人了。至于算命之学,乃唐朝与韩愈同时的御史李虚申所发明,到今也有千多年历史。也和看相同样的被人作为谋生之术,便未精先卖,不肯研究,因而也逐渐退步了。这样一来,一般人虽然相信有命理之事,也对算命看相有兴趣,但对算命看相先生却没有多大好感;因而被视为江湖之士,糊口之技,致使对此道有真工夫的人,反而不肯以此为业了。这是对中国一种极有价值的国粹之不被重视,且将因失传而式微,实在可惜!
看相之术,依中国古书上所记载的看,其灵验程度似比印度的相人,和西洋的相掌高得多。至于算命一事,则是中国独有的学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对于人生的吉凶休咎、妻财子禄、寿数等的判断,有时比看相更可靠。比如说,初生的婴孩以及未成年的童子,因为面貌体格还没有定型,就不容易看得清楚;而算命就不同,每人一出生时辰一定,这一生的祸福都注定了的。
举一个故事为例,宋朝真宗皇帝时代,与欧阳修同时有一个宰相名叫王歛若的,是江西新喻人,在周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称为江西龙虎山的道士,由他家人请到家裹替他看相。道士看了,说:此子年少登科,异日官居一品。家人问他,将来会不会破相,有没有其他的缺陷?道士却说不出来。
为什麽他的家人特意去请道士替他看相呢?原来王钦若出世三朝定时那天,因为古时没有钟錶,夜间出世的定时最难,而他就是夜间出世的,所以他就请好几位算命先生来商量,把他出生的时辰定出来。把时辰定出的时候,算命先生中有一个自号太极老人的,除被公推主笔为他定时外,还为他批命,他竟这样批道:此子年少登科甲,中年累官至宰辅,名闻天下,面貌清秀,难免有被相;其人应短小,秉性又倾巧。智慧过人,可惜好道怪诞;一生为人不诚,为官不清。命中注定,美中不足!世运所趋,贤人受厄。这位太极老人批了之后,便唏嘘三暵而去。
当时王钦若旳家人看见开头所批的年少登科甲和累官至宰辅,当然大大欢喜;但后面所批的却有所忧了。由于王钦若只是普通的人家,只要这个孩于将来会做宰相,什历也都满足了,总算得了很大的安慰。太极老人走了之后,家人就问其他算命先生,所批的话是否全对?贤人受厄,又是何解?大家都说所批的一点也没有错,所谓贤人受厄,大概当他为宰相时,有贤人被他所害的意思。
家人又问所谓破相当是怎样?算命先生说,在八字上只能看出将来难免破相,至于怎样破相却看不出的。定时之后几天,家人又请看相先生来看相。但看相先生当时只能从婴孩的一隻直衝天庭的高鼻,看出这孩子将来必是大贵之人而已,其他的也看不出来,说是婴孩相局未定,最少要待周岁之后,才能看一些。家人又因为太极老人批语中有可惜好道怪诞之语,所以到了周岁时,就去请一个龙虎山约道士,来替他看看相貌上有无学道的相,当时家人看见道士不能像算命的能够那样肯定的批来,都认为相的工夫不如算命的。
其实这并不是两者工夫上有高低,而是两者的技术有不同,看相的要成人之后有较为可靠,而临时的祸福以及迁移等,看相的也会从气色上,看得比算命的更非常准确。
王钦若后来,果然年少就被擢进士甲科,累官司空门下侍郎,到宋真宗天禧年及仁宗天圣年果然两度为相,在相貌上,他也果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面部虽有几分清秀,而项间长一肉疣,被时人绰号为瘤相,也果是然破相了。关于他其他的事,宋史曾有这样的记载: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敢果矫诞,招纳脏贿。真宗封泰山,祀汾阴,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及丁谓倡之。
原来王钦若为人狡猾,善于巴结皇上;两度为相,贪脏纳贿自肥,信道教,倡符瑞,与奸臣丁谓、林特、陈彭年、刘豕珪等,被时人称为五鬼,这也可得见其为人若何了。太极老人批命所说的为官不清和名笑天下,当是指此事的。至于当时忠臣范仲淹、欧阳修的被贬,便是所谓贤人受厄了。
就太极老人对王钦若所批的命运说,好像看八字比看相更靠得住,也更有具体的断法。的确,有的地方算命有他的特长处。比如他所批王钦若的破相一事,看相就不如看八字的。
研究过看破相命理的,那道理一被发现就不难看出。八字中有所谓成格的,如仁寿格、炎上格、润下格之类,凡是成格都好八字、好命运;但又有所谓破格,就是既已成格,而其中又有于格不宜的五行,就成为破格了。破格的八字虽不就是坏八字、坏命运,而此成格的就差得很多了。
奇怪的,凡是破格的八字必定难免脸上有被相之事,大破格的就是大破相,小破格的就是小破相,所以瞎子算命一碰破格的八字,他一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可惜,此人注定破相了!马上就使人惊奇,就取信于人了。其实这并没有甚麽奥妙的工夫的。算命也可以八字中看出人的性情、身体上的疾病,这也和看破相一样,都并不难,都比看吉凶休咎更容易。算命的难处,工夫处、在于判断八字中五行与时令的配合,谁主谁从以及其中的变化。算命或看相,都有易学难精之处,判断五行的变化,更是难精之事了。
看相的难精在于五官的配合,而更难的则是气色的分辨。这命相的高深地方。命书和相书上都只说一些原则,无法细说,所以要靠个人的天资和经验,天资高的人,但有独特的看法;经验多的人,则有坚定的判断。
对寿数的判断,就一般论,算命优于看相;但就特殊的情形论,则看相优于算命。举两个例说:清代才子金圣叹,生前算命和看相的朋友甚多。有一天他要精于命相的朋友四人替他断断寿数。两个算命的和另外两个看相朋友,把他的终寿之数都看一样,而死时不是寿终正寝也是一样;但算命的两人,只能说他非死于病和死于非命,而看相的两人,一个说他死于杀身之祸,一个说他死时身体不全。后来事实上怎样呢?金圣暵以抗粮哭庙案,清初竟被斩腰的。
再举一九四一年死于香港日军枪口之下的诗人林庚白来说。林原是一个闻名的精于算命的人,他算自己于那年有大凶,可能死于意外,于是抗战开始就由上海跑到内地去。由于他精于命理,自然对于自己的死于意外不能不担心。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在重庆住了一个时期,后来敌机时常空袭重庆,他就离开重庆。前一年他在重庆碰到友人业馀看相名家陶半梅,他们俩本是相识的。有一天他就问陶半梅,明年是否难逃大厄。那时候,他的名著命书人鑑早已出名,知道林庚白的人,都知道他自己曾说明年四十八岁有大凶的;陶半梅当然不必客气也劝他务早一年避去乡下去住,尽尽人事,或者可以逃过大厄。他问陶半梅,从相上可否看出他死于意外是可种情形。
陶半梅说:恐怕身体难免要出血;所以我劝你要到没有战争的地方去住一年,纵然逃不过关囗,能够不出血,也是好的。
当时林庚白听了,就对陶半梅说:这样看来,你们看相似乎比我们算命的更真确些,我们算命的只有两种断法:不是寿终正寝,便是死于非命,却不能确定的看出身体要出血的。
当时陶半梅也把清初看相说金圣叹死时身体不全之事告诉他,证明看相确有此高明之处。
对于断死,看相确然有独到之处,诸如死于水厄、死于火厄之类,都可以从面貌上看出来的。
我有个朋友的小姐,陶半梅说她将来要死于水厄。这位小姐当时正在大学化学系攻謓,她满不在乎,认为她既生时读化学,那末死于火也就是化学,死得更乾淨。
相书上所说的死于水厄的,乃以眉髮和脸色赤色为主,其实不尽然;那个小姐眉髮和面色都不是赤色,主要的是体形属木,而心情属火。一般初学的人,若仅仅根据相书所说,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看相要能看出体型和心相才算到家。
我的朋友也就是这位小姐的父亲,也会看相,他不懂心相与体型一致则吉,衝突则凶之理,以为他的女儿眉髮面色并不尚赤,只是性急,不该断为死于火厄。当他把这理由问我时,我当然不会说你的小姐一定要死于水,只是说陶半梅总不至乱说的。他却也看出她的女孩是短命相。我问他根据什麽?他说她是火烧性。我说火烧性的人只是俗说短命相,其实不一定短命。我就拿几位性情急躁他所相识的老人为例。他想想确有其事,就问我这是什麽道理。
我对他说,这几个性急的老人都是体型属火的人,所以性急正是长命的相。于是他渐有所悟,不久也明白他的女孩是木型的身体,人型的性情;便承认陶半梅所说的话原来是高深一层的相法。于是他怕起来了,他不想要她学化学,因为他以女儿曾说过既学化学,死于火也就是化学死。这话恐是谶语。但是,女儿没有听他的话,事实上她根本不相信陶半梅所说的话,自己也喜欢读化学。
后来抗战发生,学校撤退到乡区。由于减少员工,各部门的管理都由各系学生分派担任。这位小姐就被派管理化学器材。有一天晚上,耍烧野鸭为餚,因为野鸭身上汗毛难拔又难刮,她就取了油墱进入化学器材储藏室去取酒精烧汗毛,想不到,一不慎,酒精看火,外面人只听见爆炸一声,器材室起火,小姐就立地烧死了。
后来我们几个平日喜欢谈论命理的朋友,就把她的八字拿来研究,也略能发现她那年那月,可能死于火厄的理由。
看相对于恶死特别看得准的理由,多半是心理感应上的经验。一般人对于冷酷或凶恶的脸孔都有敏感性的认识;而这种脸谱的人又大都不得其死;所以,由于累积的经验,便有若干种型的脸谱属于惨死的,这就成为一般人的通俗相术了。
至于像体型与心相衝突属于死型之类,那不是可从一般的经验得来,要从内五行和外五行的精到研究才能发现的,这完全属于学理研究了。
我们几个朋友,从几艘轮船遇难人中,找到二十馀人的八字,研究他们死于水厄的理由。确然也能发现五行上应死于水的现象。
有几个朋友于一九四九年,由上海撤退台湾的轮船遇险中遭难的,其中有两位是上海的有钱人。他俩都是曾经几个看相先生说他是死于水厄的。于是他们决心一生不坐船不过渡。抗战爆发时,他本想到内地去,那时本来可以从陆路向内地走的,但因他一打听,说是路上有几个地方要过渡,而且听说曾经因敌机室龑翻船死过人,所以他就决定一生不离上海了。
因为不离开上海,他也很可以好好地过平安和快乐的日子,上海陆路交通便利,向西,可以坐火车游苏州、无锡、镇江和南京,同南可以游杭州、宁波,也已够逍遥此一生了。
但到了共产党要来的时候,他突然要想离开上海到台湾去了。亲戚们问他,何以突然改变一生留沪的决心,而要冒四天海行的危险到台湾去呢?他们倒有极充份的理由。他们说:看相的说我要死于水厄,但没有说定那一年要死。算命的虽然没有说我要死于水厄,却说我今年有一关口,明年又有一关口,说我今年或可渡过,明年却硬无法渡过去的。看情形,共产党来定了的,它来了,我纵然不致于被杀,而我的财产被没收那是无疑的,我如果丢去财产,我不死也要死;那时我不是上吊也要跳黄浦江的。与其死于自杀,倒不如现在离开上海去台湾,侥倖无事,我还可平安在台湾渡我的馀年,如果不幸在海上遇难,这是命中注定的,倒也算死得其所的了。
这两位朋友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考虑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就带了动产由上海登上轮船到台湾去了。真是命中注定了的,竟然船开出的第二天就遇难了!
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八字研究结果劫数难逃之说,因为他们在同一条船上遇难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命中该死的,一种是命不该死的;命中该死的虽然八字上本来确有生命危险,但不一定这在同一个月同一个日子要死的;因为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这条船上有多数的人该死,这条船,又发现确然有所谓好像就成为劫数所在了。
因而,同乘此船的人中,虽然有人不该死,但因人数太少,就无法抵挡此劫数,而自己便不能不被这劫数所波及了。我们又发现有趣的事,凡是不该死而被劫数波及的人,依他们的八字看,虽然当时不至于死,但他们大都是不再有好运的人了。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发现。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个正在走好运的人而死于劫数的。这事实就是说,凡是死于劫数的,都是该死的或是不再有好运的人,相反的就是:正在走好运的人,就不致于有枉死了。
虽然,也另有一种不该死而死的;如死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死于抗战的英雄们,除了有的命中该死的外,也有命中不该死,甚至正行好运的,那就是所谓死而不亡、虽死犹生的身后留芳百世,等于活著走好运了。这在命理上有此说法,是极有道理的。
无妄之灾 教授莫名其妙
上海震旦大学的工学院和医学院是国内很有名的。我有个亲戚程开明在震旦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留学法国,先在日本庆应大学当教授三年,又同来上海母校任教授。震旦工学院有个法国人的教授名叫卡马的,是中国出生的天主教徒,不特会说上海话,也能念中国诗。他对于中国之事知道得很多,卡马不特是一个工学学者,同时也是语言学家,他能说好几种语言。他青年时曾回法国攻读拉丁文,所以在上海某大学中也担任教授一些拉丁文课程。程开明和卡马很要好;因为他们两人对于语言学也是同志。
卡马原由程开明的介绍,准备过四年震旦聘约完满后,到日本庆应去当教授的;因而他又想学日本语。程开明在震旦读书时就学好日语,后来在日本教书,当然日语说得更好了,卡马就想请程开明教他日语。而程开明也想利用此机会叫卡马教他拉丁文,于是两人就实行交换教授。
有一天两人讲到无妄之灾这句话时,从语源去研究,发现中国文和拉丁文都有迷信的意味。中国的无妄之灾乃出于易经,是一个卦名,说明无故得咎的意思。日本的语又乃中国语又的变体,所以也以易经为根据。因为无妄之灾这一辞,引起了卡马对中国五行命理之学有兴趣,耍程开明为他介绍一个能教他粗知中国五行之学的先生;他认为这真正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一种学问。
程开明本来想把卡马介绍做我的学生,而我当时却因养病无力及此;卡马又急不能待;我就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黄先生。因为卡马在上海出生的,黄先生乘此机会要算外国人的命,就查好了卡马的正确八字,为他算了一下。
黄先生把卡马过去好几件重要的事,诸如父母去世的年月,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等等,卡马闻言大为惊奇,认为这真是一种神术,讚叹不已。于是卡马就再问后运如何,又问以后有无类似无妄之灾之事作个实例。因此黄先生就依他的八字说了两件事是近在目前,说他过了两个月,交入秋天,将有两次无妄之灾,而且情形颇严重。第二件事,说他准备四年后去日本教书之事,不特将成泡影,而且那时将有牢狱之灾。
卡马对黄先生如此推断,却是半信半疑。信的是,黄先生既把他过去绝无人知道而且自己也不留意之事,诸如父母去世的年月,生孩子的年龄之类,既然算准了,那末后运当亦能推断的;但说他四年后去日本教书之事会成泡影,同时还有牢狱之灾,那就不相信。因为日本庆应大学已和他预约了,没有理由成泡影的。同时,如果那时要生病或死亡,倒不敢说;说他要有牢狱之灾,那就不可想像了;因为卡马自信他一生不至有牢狱之灾的。
那时他难免和黄先生有些争辩,黄先生就对他说,关于四年之事,现在暂且不谈,近在两个月后之事,可把它作为根据;如果入秋之后真有两次无妄之灾,那所推断四年之后的事,你不信也要信;如果入秋后仍然平安无事,那八字就看错了,四年后之事当然也靠不住了。
过了两个月,你想卡马在上海发生了什麽事呢?那年就是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年,有一天下午,卡马由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学,自驾私人汽车出来要到英租界去,刚刚路过爱多西路英法交界之处,即上海最大娱乐场大世界门口时,中国飞机去炸日本出云舰,被舰上高射砲击中,飞机经过大世界上空,一个五百磅的炸弹脱架,落在大世界门口的马路当中,造成死伤数百人的大惨案。而卡马当时虽然没被炸死,汽车中了弹片,手面也被玻璃碎片所伤流血了。
无妄之灾!卡马驾著负伤的汽车到医院敷药出来时,心中对黄先生的算命,暗叹一声,五体投地了!第三天,程开明跑去看黄先生,也顺请黄先生替他算算命,看看有无像卡马同样的无妄之灾。程开明对黄先生明言,他本来绝对不相信命运之事的,但前天卡马之事发生了,使他不能不相信其中确有一些道理了。黄先生把他的八字一算,奇怪的,程开明的流年竟和卡马差不多,说他近十日内就有一个小晦气之事,大概是小破财。(过几天果然被扒手窃去五十多元),又说他和卡马同一月襄,也有一个无妄之灾。
当时因为上海八一三战争已爆发,他们虽然都住在租界裹,由于飞机与高射砲的关係,心中多少都有所不安,就问这无妄之灾有没有像前天卡马那麽严重,身体也要受伤出血吗?身体很可能要受伤出血,不过也像卡马前天一样,没有什麽大关係的。黄先生又这样安慰程开明:不一定都像卡马那样被炸弹炸伤,或者自己跌倒,或者在路上被人碰伤,总之,在这一月裹,无妄之灾是难免的,自己谨傎一点的,便可以大事化小事的。程开明问:若是十分谨慎的话,可以不可以从大事化为小事,再而小事化为无事呢?黄先生同答说: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谨慎到与人物绝对隔离不接触,你谨慎而他人不谨慎;你不玩物,而它偏能伤人;所以,大事化小事可能,而再小事化无事却是不可能,多多少少在那个月襄,总有些晦气之事的。
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不久,惊动全国的就是闸北四行仓库我军孤军抗战之事。因为四行仓库的后面就是英国租界,所以每日随时都有成千成万的同胞到那裹慰劳孤军,团体赠送慰劳品,个人同仇敌忾挥热泪,上海五百万人口,成年的男女,过半数曾到那裡望望四行仓库屋顶随风飘动的国旗的。
有一天,卡马自驾汽车和程开明两人也去四行仓库。因为人众多,汽车就停在很远的地方,两人并肩走到望得见四行仓的地方,就站在路边谈论战事,程开明和卡马两人正在交换学习日语与拉丁文,他们两人相约,平时两人相见,卡马对程开明说话儘量用拉丁文,而程开明则儘用日本语。他们两人就在马路边大谈其拉丁文和日本话。
有一件事凑巧的很,程开明的体型和面庞颇像日本人,又曾在日本教过书,神气也更像日本人了,因而引起路人的注意。后来又被路人发觉他满口是说日本话,于是被误认为日本仔利用西人来做间谍,突然有人喊一声打日本仔,拳脚交加,程开明和卡马两人都被打倒地上了。好在英国巡逻车刚刚过路,才把他俩救起;但已被打得头破血流了。无妄之灾,两个教授真是所谓啼笑皆非。
这是卡马第二次的无妄之灾,黄先生算命完全应验了。由于中日战争逐渐穬大,四年后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佔领上海租界,所有西人都被关入集中营。卡马全家搬进集中营后,想起了四年前黄先生的批命,说他四年后日本教书之事不特成泡影,而且那时将有牢狱之灾为之大为叹服。
善终恶死。命相同样有根据
一般人对于命运的事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死亡一定是恶运,好运就不会死,因此算命先生也常常被好运所骗,看到八字的好运时,就不再去注意有没有其他可以致死的理由了。其实,虽然大多数的人是死于恶运裹,而少数死于好运裹也是事实。
前书我们所举的王植波死于好运,便是一个好例。再进一步说,不特不是恶运,而且大多数人的死,都在好运裹不在恶运裹。如果承认大多数人都是寿终正寝的话,在儿孙满堂的情形中去世,被称为福寿全归或身后哀荣的,岂非好运?俗语说得好:生斗英雄死斗福!生的福是吃穿,死的福是甚麽昵?
就以不久前台湾飞机死难的人来说,电影界各要员的死后哀荣,绝不是平常的寿终正寝所能有,这不是死人的福吗?所以,这许多人,都是死于事业蓬勃的时候,死于众人哀悼的情况,便都是死于好运中了!如果一个人是死于恶运,就是寂寂无闻地死去,或是死于刑罚,死于众人称快!
所以,死于好运应有两种:一种是善终的所谓寿终正寝,那还只不过是平凡的好运:一种虽是不得善终,而能身后哀荣的,还算是不平凡的好运。当然最好的应是寿终正寝同时身后哀荣,那麽,这就是所谓福寿全归的了。这当然也就是死斗福的最有福了。
无论是善终或是恶死,在命理相上也同样有它的根据,一般涉世稍深,阅人稍多的人,大都能鎀分辨善人与恶人的。这就是所谓通俗相理,一个人的善相或恶相,每每显然排在脸上,一望而知的。脸面慈祥的人多数可得善终,而脸面凶恶的人,大多数不得其死,那也是事实。
就八字上言,虽然比较相术难看,但也同样有其理由可作推断的根据,只要你能注意八字上的变化,就不难看出其人善终或恶死。在南京畤,有个熟人秦君,有一天拿人命纸来找我。因为他看不懂算命先生所批的字句,要请我替他解释。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年)约六月中。他是去年出北平去南京铁道部做事的。那张命纸是北平一个姓张的算命先生批的。其中他看不懂的是五行绝者土五个字,尤其是土字何意,最为难明。
那年秦君是四十四岁,肖马,算命先生是前六年在那张命纸上拟有这样的字句:亡丁丑年八四十四岁,大运在已,经云:五行绝者土少不利西行,且宜东向慎之!
我虽然和他很相熟,他却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命运的事。他先向我声明说,他本来是不相信命运之事的;前年因为打算来南京做事,他的母亲就替他算一个八字,但命纸上批云:今年四十二岁,流年乙亥,亥卯合木南行不成,须待来年岁逢丙子,子午冲动,可得南行。
他说,前年他南京的事已经都弄好了的,只要他一来见过部长就可以。当时他不相信行不成,但结果真的因为长子结婚事不能即来,而部中这职位又不能久悬,他便作罢了,好在他当时在北平还有事做,不来也没有关係。所以就决定率性就在北平做下去,不打算来南京,因为儿子结婚之后,似乎也有和家人在北平团聚一时的需要。
但是,到了去年夏间,忽然得到南京朋友的电报,说是他的差事已经司长签上去了,要他即日辞职南来,因为他以前托朋友谋这部中的差事,他因儿子结婚不来,已经对不住朋友了;后来自己决定不来,也未曾对朋友说不决定南来了,请他不必再进行,所以现在朋友已经替他进行到司长已经签呈上去了,便不能再对不住朋友,因而他便不能不匆匆地向北平辞职,赶到南京来。
由于去年的无意中来到南京任事,便不能不使他相信命运之事颇有一些道理了。最近因为得到北平家人和朋友的来信,都说日军对于华北似有军事行动的样子,因此他就写信家裹,把这张命纸寄来,看看这裹面对于今年之事有没有甚历。现在他对命纸所批今年之事,只知道不利西行,且宜东向,而所谓五行绝者土五字,却莫名其妙,所以要我替他解释。同时,他想知道把北平家眷搬到南方来是否可行。
我把他的八字看了一下,却使我很难于开口;因为依他的八字看,今年立秋之后三个月内,秦君的寿命确然有一个大关口,而命纸所批的经云:五行绝者土,就是说他今年五行逢绝,应当归土的意思,这叫我如何能对他照理解释呢?
因为我知道秦君对于五行是外行,所以找就对他这样解释说:五行逢绝的人,应当用土去培养,所以说你今年不宜向西,只宜向东行。
不意秦君虽然不懂八字上的五行道理,却因读过多少古书,也略知五行方位之理,他闻言便对我说:是否五行以土为主,故有土居中央之说;是的;我马上就顺他的说法。土居中央。所以你目前在南京中央做事,对你今年的命运是非常合宜的。
但他又问:那塺,今年我已经在中央了,为甚麽又有不宜西行且宜东向的话呢?我自去年到了两京之后,差不多每月至少有一次东向去上海,从来也没有西行过,今年当然也只有东行不会有西行的。何以有慎之,慎之的话昵?
我就对他说,如果能保恃过去一年一样在南京做事,只有东行,没有西行,那就不会有甚麽事;不过,食这张命纸上所批的看,似乎今年有西行的可能,所以他才叫你慬慎,不宜西行的。接著秦君又问我,他想把家人接来身边好不好呢?因为我看他的八字今年确有性命之虞,到底应否把家人接来还是不接来呢?似乎没冇一个确定的理由;于是我当时只能依常情答覆他说,能把家人接求在身边总是好的,这话我并非根据他的命理说的。
后来秦君鉴于华北既有谣言,自己一时又不返回华北,就决定把家人接来。但是,事情却来得太奇怪。时同迅速发生变化。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我和他谈命只过了十几天,七七事变竟然发生了。秦君接家眷的事当然不成,从此他也再没有机会东付去上海了。
七七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我已回到上海,接看上海发生战事,时局恶化了,南京已作迁都的决定。那时南京公务员非有必要,经各机关主管长官批准的,不能随便离职。因而秦君就写一封信给我,要我给他决定是否跟随政府西迁。他信中说,若依北平张某所批的八字说,他既不宜西行,而政府又偏偏只有向西可迁,东北南三向不能迁,明显的前几年算命的已看出他今年有西行的事情了。现在依命运看,应当辞职不宜西行;但再依事实看,辞职能否获准还在其次,返回北平既不可能,他一个人将去那裹呢?
当时我看了秦君的信,真是不知如何答覆是好,因为,若依命运看,他绝不宜西行的,然而,若是我主张他辞职,可会有两件严重事件发生:第一、当时政府已在严密注意间谍问题,而秦君又是日本留学生,当此他北平有家已回不得的时候,竟然辞职不随政府西迁,很可能被视为有意通敌,不会准他辞职的;第二、他若一辞职,除来上海,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此后生活又将如何呢?
因此我的回信并没有替他作任何的决定。我只说两点:第一、我在命理上的看法,和他那张前几年在北平所批的命纸上所说的一样,没有新的看法。第二、就目前情形言,既然回家不得,又无退路,事势非随政府西迁不可。那末,动不如静,逆不如顺,不辞职是静,跟随政府是顺,我这话也都是事实,并不勉强说的。
当时我心裹会这样想,如果秦君今年命中当死,就是中日战争不爆发也会死的,而今能跟随政府走,在政府的保护下,不是比之个人奔走更安稳得多吗?当时我面对他的八字,又面对当时的局势,死生问题原无足论,而他的八字今年不宜西方而偏非走西方不可,这就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奇妙安排了!
果然不久我们知道政府已从南京西撤至武汉;也知道秦君跟随政府平安向西去了,从此他也不再来信。我们由报纸上以及传闻中,知道政府西迁之后很是安全,并未受到敌机的大轰炸,私心也替他欢喜。
有一天,我閒著无事,无意中把秦君的八字拿来看看,发现那年夏曆十一月是壬子月,十三日是丙子日,八字中的用祌被冲剋太过,当是死亡之日。那时是十月底,我就写信给一个朋友,他是和秦君同司的同事,朝夕相见的,我请他儘可能告知秦君,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千万要足不出户,并请他儘可能帮助秦君,那几天不派他公出,留在部中申办公。因为这位朋友是秦君的上司,此事只有五天的日子,他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又请他不必把这五天,尤其是十三日那天的大难日子告知秦君,怕他因心理作玥,反而发生其他不利的事,我希望此信能于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到达,就用快信发出。
信发后我一面等待朋友覆信,一面又推断秦君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如果不能逃过鬼门关的话,应是善终还是恶死呢!我知道秦君素有胃溃疡病,如果是善终!最可能因舟车劳顿加上水土不服,胃病发作而又因医药不便而死亡;若是恶死,那就是出于交通失事或被敌机轰炸而死。当时我对于八字上的死亡问题还在研究而没有甚麽大心得,本来死亡在八字上就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有的八字可以明白断定他何月非死不可;但此种八字好像只佔百分的四十;约有百分之二十,可以看出要死于那一个运裹的五年之内;尚有百分之二十,则不可能看得准的。秦君的八字虽然属于头一种,就是事先可以看出是乙丑年十一月确有死亡的大厄。
可是,虽然我能姼看出他那年那月死亡的大厄,却不能看出到底是善终还是恶死。
因为当时我已经学了相术,我知道在相上显然有善终与恶死的相格的;那末论理上也一定有此命格,而且命书也略有提到的,不过不像相术那样具体而确定而已。于是在我的朋友没有覆信之前,我就和两个精于命理的朋友,对秦君的八字加以商讨。
商讨的结果,大家断定秦君在十一月十三那天当死于非命,理由是用神的衰神被旺神所冲,而四柱岁运又多冲剋。这一结论并非理论,也不是完全根据命书所说的,这是我们几个人,一面根据命书中死亡的五行原理,一面根据许多熟人的事例作为根据的。
自旧曆十月二十几我发信,直到十二月半才得到朋友的覆信。来信说,他因政府机关迁移不定的关係,接到我的信已经过了十一月十二一日,是十五日的下午才接到信。而秦君和部中另外两人,是十一日上午被派外出,约需一星期才能同来。当时他想十五日以前既然没有得到关于秦君有何事故的消息,则十三日秦君想是已告平安无事了。真是奇怪,第二日即十六的清早,就接到和秦君一起公出的两人来信报告,说是十三日中午秦君在公路上被敌机机关枪扫射身死,已由当地机关负责收殓了。
秦君死于非命的事实给了我们研究命理的人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从而确定同是死亡,何者死于非命,何者属于善终,就是恶死也有死有馀荣、死有馀辜之别。
见色不淫 桃花化为财运
现在老梁是老陈的上司了,他是维新政府的首领。为著天一星说准了他的命相,有一天派人送给天一星白米十包,现金二千元表示谢意,并约他便饭。吃饭那天老梁并没有邀请政府的要人,因为这是私人间的酬酢,而且对方足一个算命先生此事又是迷信之类,所以他只约了几位自己的亲信,大都是机要秘书,总务科长之类。当然,老梁的用意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请天一星替这小群自己的心腹看看相,是不是六亲同运,最重要的请天一星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冲剋;因为那时抗战的地下军事人员正在上海展开暗杀汉奸,老梁深怕自己心腹中有问题,那就太危险了,所以在入度席之前,他曾嘱天一星替他留意今天一起吃饭的人,对他有无冲剋。
于是在吃饭的时候,天一星就对同席的各位相局和气色都留意细看一下。当中有一个姓杜先生,仪表十分出众,年纪大约三十出头,天一星问他说:“杜先生,你今年贵庚?”他答说:“三十四。”天一星又问一个姓萧的:“萧先生你的贵庚也差不多吗?”他答说:“我们两人同年,我比他大三个月。”接著他们两人就同天一星请教,最近这几年后运如何。天一星笑笑地说:“今天梁先生赏饭,各位又都是梁先生的亲信,我当然用不看说各位都是贵人相;但我们既然有此一面之缘也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得看看各位有没有什麽地方,需要对各位之中有所贡献。”“对的,君子问祸不问福,我们这一班人,都是叨梁先生的洪福的,目前当然都不错。”有个黄先生这样说:不过,目前的时局对我们是不利,所以我们还是问问此后我们的安全第一问题。”“先生,你看得出这战事要到什麽时候可以结束呢?”另一个人这样问:“这战争到底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看来总是有害的,战事那有对我们有益的道理呢?”
天一星先生又笑笑地说:“那也不一定,凡是有利必有弊,战事所以之发生,原因由于双方都认定对自己有利的,所以才会爆发战争;但事实上大都是两败俱伤的。至于这场对于各位的利害问题,依我的看法,则是对各位有利的,我看各位的相,都是由这场战事而转好的。”这句话把在座诸人都说得好笑了,他们心中想他们都是一班小新贵,的确乃由抗战发生才有这机会跟著老梁参加这伪政府,于是他们就关心问到战事的结局问题。”关于战事的结局如何我是不敢说的”天一星说:“但我从梁先生以及现在从各位的相局看,这战事要到八年之后才能结束的。至于如何结束。结束时对各位的情形如何,我也不知,到了那时,各位自然会明白的。”接著那位杜先生就问:“先生,刚才你曾特别问到我和萧先生的年龄,是否有什麽特别事故?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希望你能不客气地指教,我们是问祸不问福的。”
天一星又笑笑地说:“你们虽然要问祸,而我却是为你们二人说福。不过,福也有多种,有的是洪福,有的是清福,也还有是浊福的:洪福像梁先生这样是难得的,一般人大都是浊福的。”他看了杜先生和萧先生两眼之后又说:“我看你们两位特别喜欢的还有一种福:我想你们各位也许会晓得杜先生和萧先生有什麽特别福的!”
于是他们当中有的说他“食福”很好,也有的说他“衣福”很好,因为萧先生当时就穿著新裁的笔挺西装,也有一个说他俩还有一种福,但他不肯说出来,因为那福是许多人不知道的,而他本人也不愿意人们知道的。
“对了,我说的杜先生和萧先生的特别福就是这福,是你年轻的人都喜欢的“艳福”,对吗?”天一星先生说了之后,大家都笑起来。而杜,萧两位呢,却也难免脸皮有些发红,笑嘻嘻地已在承认他自己的艳福了。
“不过,”天一星先生说:“艳福地分正与邪两种:正的艳福是妻贤妾美,而邪的艳福则是寻花问柳,到处风流,最重要的,正以艳福对财运有利,而邪福则对财运有害,甚至有其他灾祸,所以有艳福之人不能不谨慎了!”
杜、萧两人肚子裹好似想问什麽,而咀裹又说不出来样子,还是刚才说硗得他两位有特别福的那位先生就说:”那末,请教先生,他们两位到底是正还是邪呢?”
天一星先生说:“我刚才特别问他俩的年龄,就是为了这事,如果他是正艳福,在命理上也就是正桃花,那就不用说什麽了,就是因为他们两位都不是正福,同时是有灾祸的,所以我才特别要请他注意了。”
那人又解释说:“但他似乎也很快乐,他的太太很大度量,不大管他,并没有什麽麻烦之事发生过。”
“是的,”天一星说:“在他三十四岁之前不会有什麽麻烦,但明年起,他俩开始行眼运,在三十五至三十八岁这四年中,他必定有新的桃花运,如果不想避免也像过去一样的话,那灾祸便要立至的,如果今天肯接纳我的话,明年起,对新的艳遇,力求避免,那末,逢艳退避,见色不淫的结果,不特一切顺遂,还可能逢艳化财,官运财运都会享通的。”
此时杜先生就开口问:“先生,你看我们两人是否因为是同年关係,所以都有这毛病?我们两人的情形是否以后都是一样的?肯避免的话,是否可以避免呢?”
“如果肯避免,总是可以避免的。“天一星说:“不过,依你们的相局看,彼此却有不同之处,杜先生的艳福大都是飞来的艳福,是女人对他有意的:而萧先生的艳福则大都是招来的,是他对女人施展手腕的。”
说到这裹,在座中各人都哈哈地笑起来,表示天一星这话又说对了。萧先生自己听了难免脸红耳赤觉得没趣。
但天一星却又接著说:“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命相注定的了,没有办法的,各人有各人的不同艳福。在座各位之中,有的人很想有艳福,但不特一生得不到美人的垂青,就是自动地愿做美人的奴才也还没有福气的。”大家又大笑起来了,因为其中确有一个姓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常常碰女人的钉子的。
“他们两人还有什麽不同的没有?”其中有人这样问。“以后你们两人同样都是灾祸的吗?老杜既然是飞来的艳福,那末他是否可以免于灾祸呢?”
萧某又说:“我老是不肯避免的话,可能有何种的灾祸呢?不太严重吗?若是这一切都与命相关係的话,为什麽又可以避免的呢?”
天一星此时似乎正经地对他们解释其中的道理。他说:“本来飞来的艳福和招来的艳福是有不同的,招来的当然不如飞来的;如果一生只有一两次飞来的艳福,而能守住这艳福,那就一定属于贪色与好淫,而灾祸也就难免了。”他加重口气地说:“大家要知,艳福可以飞来,横祸当然也可以飞来,而且比其他横祸都严重。”
“我们两人是否明年就有横祸?是旧事所引起的横祸,还是明年新事所引起的横祸?”萧某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旧事,而是新事。”天一星说:“我不是说过的吗,你们两人的平安艳福只到今年为止了,明年以后,开始走眼运,就不可再有女人之事了。过去,你们两人都是从二十四岁起走桃花运,已经走十年了,对吗?”
杜和萧两入,默默地想了一下,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天一星所说的并没有错。天一星就继续说:“我可以断定你们,这十年来,你们两人没有做好的事,除女色之外,其他的事都是不满意的。而且,你们两人也不曾做过足两年的事,都是几个月至多的也不过一年几个月就要变动的;因为你们差不多每两年就有一次艳遇。”
“明年夏天起,如果再有艳遇之事,千万不可太随便了”天一星继续说:”在这四年中,就是从明年二十五岁至三十八岁,如果仍旧见色思淫的话,不管那艳福是招来的也好,飞来的也好,其所造成的灾祸,不仅破财而已,最少要伤害身体,要流血之事,甚至杀身之祸!”
那天在宴会席上,天一星对杜某萧某两人所作的断语只此而已。他只是指出其利害,并不加以断言两人将来是如何,因为依他的看法,这灾祸是可以避的,但老不想避,那就只有任其发生灾祸了,轻的流血,重的杀身。
第二年的春天,老梁到北平去和“临时政府”的首要举行会议,他是代表南京的“维新政府”的。他原是一个老风流人物,又曾是北洋政府的政要,此次到了北平,又以新实的姿态出现,而”临时政府”诸首要又大都是旧官僚军阀,于是若干天的会议之后,就是在花天酒地中酬酢了,老梁自己也想不到,竟然看中了一个二十一岁的妓女,在临时政府诸政要的捧场之下,用八千元的身价把她赎出纳为小星了。纳妾的仪式就在故都举行。
几天后,由北平一起坐日本的专机回到上海,老梁把她藏娇于上海北四川路底虹口花园附近的窦乐安路的金屋裹。这地方有几所花园洋楼,上等住宅,路上既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站岗,而各新贵的住宅门口又有维新政府的警察把守,出入有保险汽车,再有保镳随从,这藏娇之地总算最安全没有了。
老梁纳妾的喜讯一传出去,新实们当然要向他庆贺一下的。请客那天,老陈也由杭州赶到上海。触景生情,老陈想,自己和老梁的年纪差不多,他已有妻又纳妾,而自己自去年那位黑巿夫人捲逃之后,还是孤孤单单的。
此时,老梁是老陈的上司,上行下效,老陈不久也婜了一个上海会乐里的妓女为外室。因为老陈元配在世,而且生了三个男孩,很有权力,老陈只好偷偷摸摸的在外窒藏娇,却不敢公开纳妾。
南京到上海和杭州到上海的路程差不多,都只是几个钟头的火车可以到达的。所以老陈的外室也设在虹口区,为的是他们各家彼此可以照应,而她们之间也可以在老爷不在家时有伴,来来往往。
凑巧的是,当时伪组织的上海特别巿巿长傅某被抗战的地下工作人员暗杀掉,上海特别巿政府改组,南京维新政府就派人参加。这上海特别巿政府是成立于南京维新政府之前,直属于日本军事机关的。所以到了此时一南京维新政府才有机会派人参加。除由日本人同意派二三个上层的人参加外,也派几个科长级人员参加。而杜某和萧某二人,因为对上海社会颇熟悉,就被派来当科长了。
这两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小新贵,除巿政府科长的职务外,为著各种便利,他俩就负责平时照顾虹口各区政要的公馆,以及每次接送南京和杭州两地的政要事宜。因此,杜某与萧某二人,就很自然的和政要的家眷有接触的机会了。
那时候,虹口区内南京和杭州两地新贵的明暗外室约有二十家之多,家家都需要杜科长和萧科长的照顾,一时这两位科长便成为二十家的红人。很快的,他们两人便成为虹口区的姨太太们的忙人了。他俩日夕都在这群雌粥粥之中奔走,无形中,有点像小女人国的两个男子了。
最初还是萧某向老陈的外室施展弔膀子的故技。老陈的外室小名紫萍,原係会乐里的妓女,老爷既然常在杭州,她独居虹口难免孤寂,于是一拍即合,萧某果然又走桃花运了。老萧虽然见色思淫,故态复萌,但他也不曾忘记天一星去年对他所说的话。
但他又环顾当时的环境,当时暗杀风炽,老陈每次由杭州来上海必先打长途电话通知家裹,再出家裹电话通知老萧,由他带了保镳和汽车在火车站接他的。此事不会被老陈识破的。
同时,他知道自己和老杜二人是虹囗区的一号红人,而平日和各家中的下人们也极其相好,而且,关于姨太太交男朋友之事,在上海单是一种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之事,就是被下人们看出,也不至于有什麽的。这老萧的想法自认并没有错,在他的势力区内不至于有灾祸的。
和老萧差不多是同时,老杜也果然又有飞来的艳福,而且同时飞来约有三个之多。三个女人是夏太太,周太太和梁太太。真想不到,这位梁太太就是老杜上司老梁由北平娶回来的爱妾。她原是苏州荡口地方道地的美女,自幼被父母卖给北平鸨母当妓女的。苏州是出美女的有名之区,而美女即不是出于苏州城裹,而是生于苏州西南面一个名为荡口的乡村一带。上海和北平,天津妓院裹的鸨母,每年都亲自到苏州来选拔美女作为养女的。当然,谁也都知道凡是来苏州卖女孩的,都是预备长大当妓女的,所以大都向荡口地区去选择。
这位梁太太既係荡口的道地美女,又曾经鸨母的训练,再当过名妓的经验,当然在色艺各方面都是八面玲珑的;只要她心中有意,就让十个的老萧?也不能逃出她的迷魂计的。不过,现在却有一个特别的情形,那就是老萧这时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她们群雌粥粥的心目中,因为她们的老爷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便成为一个年经的美男子了。所以,除了梁太太之外,还有两位也都是姨太太。
而且,这两位夏太太和周太太,也都是堂子出身的名妓,同时也都是苏州人。因此,由于三星随月的关係,她们之间彼此既有顾忌,而老萧也弄得无所适从了。
老萧本来是一个风流的人物,虽然他一向都是女人来垂青他,而他却也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但此次情形即有些不同,因为她们都是彼此时常相见的太太们,而且也都住在虹口区附近的地方,在她们之间老萧的一点举动她们都会知道的,”人言可畏,此事若被人传到夏,周,梁三位大人知道,别的不敢说,科长的职务马上就要丢掉。因此,老萧不能不顾忌,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周旋于三星之间,却始终于不敢作进一步的尝试,和她们仍保留多少距离。
有一天梁太太率性不客气的直接问老肃,何以对她若即老离?是否他喜欢夏太太不喜欢她?是否因为周太太对他有什麽特别的地方?老萧一时答不出话来。逼不得已,只好把从前算命天一星说的话说出来塞责了。他对梁太太说,因为去年梁公请客时,算命先生天一星,也就是前两年预言梁公会东山再起的人,说他今年有桃花运,但这桃花运是有危险的,所凶他不敢尝试了。但这话不能使梁太太相信,他认为这只是搪塞的话,一个男人不会因为相信命运的话而拒绝女色的。于是梁太太就要求老萧一道去算命,看看是否这样说。老萧当然不能不答应,就说要到天一星那裹去。
然而,梁太太却另有意见;她说天一星未必可靠,同时,他既然替老萧看过了,当然要和从前的说一样。她主张到霞飞路张荧堂那裹去,因为,张荧堂是一个瞎子她认为瞎子比开眼的好,他是铁口直言的。
于是老萧只好陪梁太太到张荧堂那裹去。老萧把畤辰八字交给梁太太,他自己预备不开口,只是听,梁太太把老萧的生辰报了之后,张荧堂就问:“小姐,这位先生他本人在这裹吗?他是你的什麽人?”
梁太太看一看老萧,笑一笑,她好像很得意地表示她之所以选择张荧堂,就因为他瞎子看不见人,他的推断命理就不至有何顾忌了。于是她就随口依她早就预备好了的答:“他本人不在这一裹;出门做生意去了。他是我的哥哥,想今年娶嫂嫂,看是否合宜。”
张荧堂屈指在点算,仰起头来微笑地说:“不对的,令兄已经有了嫂嫂,而且有了两个儿子,今年不会娶亲的,你不要骗我。”他再坚定地说:“他既是上海人,今年并没有驿马,不会出门的。同时,他这个命也不是做生意的命,而是做官的命,目前官虽然不大,但他的权力却是很大的。他的情形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末他的八字就没有错,我就可以再说下去,否则就是八字错了。”
此时老萧和梁太太相对一笑。梁太太笑笑地表示承认张荧堂的论断,说:“先生,你说的没有错,请你再说下去。
“小姐,你用不看骗我的,我也无法骗你的,你来为的是替令兄看今年流年的运气,现在已经五月了,本年的事已经发生了不少,我只能就命理论断,说对了并没有什麽希奇,说不对才算希奇。现在让我先把过去五个月的情形说一说,如果说对了,那末以后的七个月也会对的。”张荧堂特别问一句:小姐,你真的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太太吗?他的太太也在这裹吗?
“我是他妹妹,我的嫂嫂不在这裹,”梁太太说:“有什麽话请你随便说,你只是照命理说的,是好说好,是坏说坏,没有什麽关係的。”
于是张荧堂说:“令兄几个月来正在走桃花运,看他的八字,显有拓合和争夺之象,似乎有两个以上的女人向他争夺。不过,截至目前,他还是徘徊两美之间未有所抉择。此事希望不要让你的嫂子知道,知道了,也要劝她不要加以干涉,反而有利,让他良心良知发现,可能脱离这桃花的劫煞的。因为走桃花运的人,心志难免胡涂,家花不比野花香,太太一干涉,反而把他迫上梁山了。”
“那麽,据你看,他是可能脱离这桃花运吗?如果不能的话会怎样呢?”梁太太问:”如果他能逃过这美人关,又有什麽好呢?那两三个女人之中,是否都不会达到她们的目的呢?她们对他也有什麽不利的呢?”
张荧堂说:“今年是令兄交运脱运的流年,所以今年是难免有重要事情发生的,现在他碰到了妒合争夺的桃花,就是不利的现象,如果不慎,便有劫煞;如果能避去这劫煞,这桃花就会转化为财运的。”他又屈指扣算一下,说:“由昨天起,四十五天之内,将是他的重要关头,若能保持现状,不因女人之事损德,那就会有飞来的财运;如果有缺德之事,也就是见色思淫之类,那就有飞来横祸的,希望你想法告诉令兄,无论如何要渡过这四十五天。”
老萧听了就对梁太太看看,眼色的表情是向她请求原谅,让他维持现状”乐而不淫”,看看四十五天之内有何好的变化。梁太太看见张荧堂说得这样确定,时间也在目前的月半之内,也就无话可说了。
事也奇怪,就因为梁太太自己听了张荧堂的话受了感动,就决心把老萧放弃,让他免于不利之事而且又有财运好走,便主动地把算命的事告诉了夏太太和周太太,说是大家既是好朋友,也都对老萧好感,就当让他走好运。
因为此事原是三个女人成为鼎立之势,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也有各人的顾忌,现在既然梁太太肯把此事说破了,夏太太和周太太当然没有话说,因为此事原不能说破,现在既经说破,大家就无所谓了,男人她们并不是没有见过的,何必一定要老萧呢。于是大家就决定不再与老萧来往了,老萧也乘此机会从此不再和她们混在一起了。说也奇怪,此事还没有一个月,老梁和老夏老周三人在南京接到有人的告密信,说老萧和三位姨太太有说不清白的事,老梁本是一个风流人物,从前在北洋政府时代,姨太太偷人乃极平常之事,只要不把丑事闹出去,原无所谓的。但老夏和老周二人都不然,他俩决定对付老萧。
过几天老梁回到上海,所目见和根据公馆裹的用人报告,老萧已不到公馆了,和姨太太并无什麽不清白的事。有一天他见到老萧,就问老萧何以不常到公馆去?老萧也直说:“人言可畏,我要避嫌。”
老梁说:“只要我相信你,何必避嫌?人言何必畏?”他说:“我记住去年天一星算命的话,我今年又有桃花运,而且是有不利的劫煞的,所以就是梁公肯相信我,也不能挡得住劫煞,因为这是灾祸,是旦夕难保的天灾人祸,谁也不能保证的。”
这话却把老梁提醒了,因为在南京时老夏和老周会对他说过此事,而且当时他们两人曾说过,老梁度量大,不想对付老萧,而他两位决定对付老萧的。于是他当夜电话约夏周二位见面,问他对老萧之事有没有什麽决定。他们二人说已经决定了,是买了一个法租界裹的流氓,预备绐老萧吃吃苦头,意思是要打伤他的身体,如毁容之类,最少也要使他进医院半年。
老梁立即要夏周二人把此事暂押后两三星期,等他查明白了再行不迟,如果确有此事的话,乾脆就把他干掉算了,何必拖坭带水呢。夏周二人当然要接纳老梁就话,通知凶手暂缓两三星期之后,等通知再决定。
过两天一个晚上,老梁就和姨太太谈起夏太太和周太太为人之事。三句话说完,老梁有意的说到老萧身上来。老梁说,夏先生和周先生为了不放心他俩的太太年轻美貌,曾派有密探时常暗中看守他们的家;根据报告,老萧和两位太太过从甚密,似有暧昧之事,所以他们两位要想法对付老萧,就问姨太太,他们之间,到底有无可疑之处?梁太太一听见夏周两位要对付老萧,她知道所谓对付是很严重的事,即上海流氓所谓”白的进去,红的出来,”就是要暗杀的,于是她就对老梁说:”如果夏先生和周先生要对付萧科长的话,那末真是冤枉的事了,而算命的话也不灵的了,做好人也没有用了。
这话当然引起老梁的注意,在追问之下,才明白老萧确然因怕有桃花运劫煞而不敢和她们三位姨太太往来的。老梁既然明白了这事,但因这话乃由自己的姨太太而来,当然不能使夏周二位相信,暂也不告诉他们二位。
过几天老梁对老萧说,想把他再调南京去任科长。老萧毫无考虑就答应了。接著老萧连上海的家也一起般到南京去了。因为南京那裹的科长此不上上海特别巿科长的肥缺的,老萧竟然决心连家都带走,可以证明他确然是怕走桃花运的。老梁此时才把老萧
发布于 2024-08-25 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