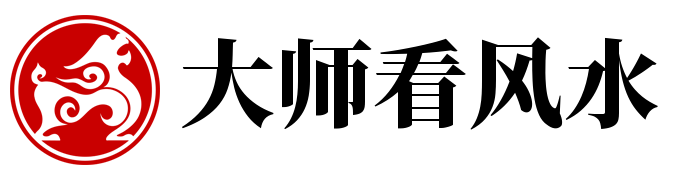李姜洁:如 风(散文)
如 风
李姜洁
迎面来了一阵风,风里带着寒意。冬已至。快递小哥戴上了围脖和手套。我不用,到办公室,步行也就十几分钟。“这娃以后是要上大学,要坐办公室的。”三岁那年的一天,我正趴在大洗衣盆旁玩肥皂泡的时候,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给“咧个天生福相的娃”算了一卦,据说喜得我爷爷当即给了算命先生五角钱。
在七十年代的农村,仓库保管员、记账员,不用下地也可以挣工分,就相当于“白领”了。听大人们说,小时候,我长得胖嘟嘟的,又是个慢性子,因此隔壁三婆婆常说:“小胖胖,你看你一天走不了三里路。你要加紧读书,长大了坐办公室啊。”
十七年后,我真的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过上“坐办公室的”生活的娃。那年春节,我爷爷破天荒给了我和我们家族第一个重孙——我的侄儿,每个人五元压岁钱。我爷爷叼着旱烟袋,从衣襟的斜口袋里掏出分辨不出颜色的旧手绢,拣出两张五元的,又不紧不慢卷起来放进衣兜。不知怎的,我得到五元压岁钱的消息,这个春节还没过完就被我爷爷众多的孙子孙女知晓。多年以后,在我爷爷的灵堂上,我表哥认为,我应该守灵一夜,并且给打丧鼓的师傅最大的“利是”,因为爷爷给过我五元压岁钱,对我最偏心。
可惜,我爷爷一辈子也没到他最偏爱的孙女所在的城市看看。在当年的家信里,我写到这座叫“宜都”的城市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街道到处干干净净的,就像家门口的道场刚刚刮过一阵风的样子,一片树叶都找不到。
我爷爷是扬谷子的能手。对于风向的把握,就像对他旱烟袋里烟丝的好坏一样,看上一眼就心里有数。那年春节返乡,有一天,我正坐在家门口的道场上,闲观亲戚们打牌。时不时地,从平坦开阔的远处,刮来一阵风,又干又冷。而自从生活在那个山水环抱的城市后,我早已不习惯平原冬天这种一马平川的风。“要说呢,还是宜都好……”话一出口,我觉得有些愧疚,坐在我爷爷亲手打下的道场上,仅仅因为风,就开始“数典忘祖”了,是不是对不起我爷爷呢?
随着“户户通水泥路”铺展到我家门口,我爷爷打下的道场只留下了屋檐以外的五米。我幺叔从这条路出发,带着全家到浙江打工,第一次看到了大海,吹上了海风。而我十多岁的表弟,对仅凭一个按钮就能托运无数人上下的电梯更多充满了探究的兴趣。他于是选中一座大厦,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呆在电梯里,无数次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直到大厦保安发现异常,把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子”从电梯里揪了出来。
而我爷爷打下的道场边立着的六间瓦房,正被风、连同雨,一点点剥蚀。当初村里最亮堂的房子,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手掌。就像我的父亲,有一天终于表示愿意将老屋挂上铁锁,移居到两个孩子所在的城市养老。房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已没有精力侍弄;院墙外那些李子树、橘子树、梨子树,只能和鸟儿们做伴了。这个当过兵的人,没有向敌人投降,却被岁月缴械。父亲的老朋友们,像风吹蒲公英一样四散开去,偌大的村庄,偶尔有一两只狗在闲逛,看上去没精打采的。没有孩子和它们追逐玩闹,孩子和狗是天生的玩伴。儿时,我家那只皮毛发亮、体格健壮,名叫“赛虎”的黑狗,是全湾狗的“老大”;因为聪明,也是全湾孩子的“萌宠”,虽然那时的农村,还没有“宠物”的说法。
可是,那样热气腾腾的乡村,那些温暖的乡野物事,却是消逝在了风中,一去不复返了啊。
自从父母搬离老家,我好些年没在老屋住上一夜了。以往,家里的床铺垫着新打下来的稻草,蓬松透气,翻个身就呼呼作响,睡上去的舒服程度比任何席梦思都不会差。现在,家里早没有稻草,最关键的是,没有用上天然气,打开水龙头,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特别是洗澡,要在盆子里擦洗,简直太难受了。我爷爷如果还在,他可能会像以前一样念叨着:“娃子们,这点苦都受不得,变修了哟……”然而,儿时小伙伴们嬉戏的水塘、门前空地上蓬蓬勃勃热热闹闹的牵牛花太阳花指甲花、三爷爷二婶婶幺婆婆那一张张温暖慈祥的面容……这些故乡的场景,越来越多地醒在我的梦中。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很老了,因为据说老了容易怀旧。何况,我本来就是个容易怀旧的人,又怎会不怀乡,怀想自己出发的地方?
我不知道,对于我家那个“风一样的女子”,以及零零后的那一代,从她们的手机飞速划过的画面里,有没有一个词,叫做“乡愁”?我在她的大学开学自我介绍里读到:“我永远怀念生活了十二年的小巷,怀念街角卖冰棒的小亭子,怀念吹着旧式电扇看电视的午后……”在她小学三年级文章即被发表、在各类征文比赛中频频获奖,感受到她的文字间的灵气之后,我曾倾力于将她引向文学的道路。而她,在反叛的年龄,开始越来越多地和我针锋相对:“不要试图把我、还有你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培养成作家!”钢琴、动漫、绘画、唱歌……她对无数新鲜的事物发生了兴趣,直至跳上街舞,直至“爱死了街舞”。她正越来越像个男孩子的样子,看上去很帅,却越来越和我希望中的淑女的样子背道而驰。“像风一样自由,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街舞。”她说。
像风一样自由,而自由的风也给她以及她们那一代吹来最前沿的信息以及无数热词。从“修勾”到“凡尔赛”到“内卷”……前几天,我在她的朋友圈看到一个叫“严酱”的词,以为又是什么新潮的热词,曾就此拜访了一下度娘,结果一无所获。她的微信头像经常更换,让我极不适应,有几次,甚至改了名字,只是“因为好玩”,而这种更改,使我感觉她在我的千人朋友圈里显得陌生。直到有一天,我笑着告诉她:“爸妈现在老眼昏花了,你老是把头像改来改去的,我们会把每月的生活费错打给别人的。”“好吧。”电话那头,她也笑了。
不得不说,在和孩子平等沟通方面,我的进步挺大的。我努力跟上女儿的节拍,和她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我当然不再是孩子儿时心中“家庭总管”的形象,现在,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这个形象了。我向她学习新事物,她甚至教我学习如何应对挫折。“遇到事情,你老是不肯放过自己”,她说,“为什么不能学会和自己和解?这不是妥协,这是迂回的智慧。”
俨然,我们的角色已开始互换。
随着女儿在大学享受自由的风,“留守之家”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于是,我们去兜风,用更多的时间,就像以前一样。
有时,我们骑上那辆摩托。这辆摩托确实够旧了。它和它的主人一起出现在我面前时,它的主人还算得上个帅小伙儿,它也锃亮炫目。它每天在下班时间准时出现在我的单身宿舍门口,载着它的主人以踏实可靠的形象俘获了一位少女的芳心。
就是坐上这辆摩托的后座,我去瞻仰了“宜都”牌坊书法题字,去欣赏了长江和清江奇妙的交汇之处,去探访了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江边的故居……直到有一天,我对酸东西馋得要命,特别想吃桔子,而那时桔子还挂在枝头,硬梆梆的。于是我们骑上摩托,跑到江边,在不知谁家的树上摘回几个桔子,回家砍开狠狠抿上几口酸水,算是解了馋。也许再没有谁对桔子馋到要砍着吃了,可是肚子里有个天生就嗜爱桔子的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女儿知道的,时常坐车出去兜风的,仍然是“三口”,她,换成了那只叫“丢丢”的狗狗。狗狗是她从“流浪之家协会”抱回来的,狗狗的名字也是她取的。“人家不要了的狗狗,就叫丢丢吧。”抱回来的路上,女儿就把名字想好了。后来,随着这个小生命在我们家赢得越来越多的宠爱,它有了各种昵称,就像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被赋予各种爱称一样,而它居然对各种昵称都能及时回应,好像它是我们的孩子似的。
对于这样的家庭地位,它的“馨馨姐姐”有时会有点“吃醋”。不过,说是“吃醋”,也就是嘴上说说罢了。有了它,老爸老妈会增添许多欢乐,女儿知道的。夏天兜风,它更喜欢坐摩托,虽然摩托已经很老,老得一公里外它就能听见摩托的马达在拉锯,老早就开始在门口哼唧。夏天的风,很爽;它探头看着流动的街景,毛发在风中飞舞,很酷。冬天,我们就开汽车去兜风。不管有多冷,总是要大开着窗的,不然怎么叫“兜风”呢?最关键的是,它肯定是不答应关窗的,它是要把整颗头都露到外面才肯罢休的。
最近,我们去“宜都长江大桥”去得最多,并带上那个小家伙,开启了一次关于宜都桥迹的旅行。
从已然开始苍老的清江一桥,到宜洋一级公路跨越清江的清江二桥;从承载了特殊历史使命的枝城长江大桥,到双向六车道、在建时速最高、线路最长、打通了“宜荆荆恩”城市群南北交通经脉的跨长江大桥——宜都长江大桥。驰行大桥,如入蓝天白云,丢丢兴奋的吠叫在风中传到很远很远。
“如果宜都当年有这样四通八达的桥”,在看到“宜都清江三桥”正开足马力推进、2023年10月即将建成通车的消息,我又一次回想起数年前,当红色摩托的主人还是个帅小伙儿,正在俘获一位少女的芳心路上的囧事。帅小伙带着少女从宜昌耍了一圈回来,从红花套下了轮渡回宜都。那时候,还没有“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来往宜昌,得坐船往返。下船后,糊涂小伙径直走上前往五峰的道路,而那个只知道“前后”“左右”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憨憨乖乖尾随。直到从帅小伙变成“老帅哥”,提起这事,他仍然认为,是那些五峰的客车司机“不够地道”。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两个要去宜都的人走错了道儿,却没有一个司机提醒,直到他自己发现?
“因为看见你正带着我,怕坏了你的好事……还或者以为,这是两个憨憨。”我大笑。
车行之处,路边住户的阳台上挂出的红彤彤的香肠、成串的腊鱼,宣告着春节将至的消息。该备些年货了,何况还有个“吃货”即将返乡——
“好想吃宜都的橘子,就再多多买些橘子吧。”每年秋天,我都要给女儿寄几箱宜都的精品蜜橘,让她和同学们分享。从“中国柑橘之乡”出去的娃,当然只有最好的橘子才能满足她的味蕾。我告诉她,现在,宜都当地的“果冻橙”正上市,皮薄肉厚,入口即化,爆浆无核,是可以吸着吃的橙子哟,快回来一饱口福哟!
丢丢已经越来越聪明,能够听懂“馨馨姐姐”即将回家的消息。这个消息让它开心到转着圈追赶自己的尾巴,直快到让人眩晕。因为这意味着,它又可以坐上汽车,去气派亮堂的宜都新车站接“馨馨姐姐”回家啦。在那里,它可以在开阔整洁的广场上尽情地打滚、撒欢,而在“馨馨姐姐”走出车站大门的那刻,朝着那个温暖的怀抱,箭一般飞奔,像风一样自由……
相关推荐
-
按生辰八字起名测试
自古以来,人们就特别关注自己的出生时间,这也衍生出了按出生日期命名的传统。生日八字命名测试是通过分析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地点和性别信息来确定八字中的五种元素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取一个吉祥的名字。这种命名方.. 点赞2025-04-24 07:34 -
梦见马蜂窝掉下来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预兆
有时候做了梦,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梦见马蜂窝掉下来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预兆?梦见马蜂窝掉下来是什么意思:梦见马蜂窝掉下来,预示着运势不错,最近会有喜事放生,是祥兆。梦见马蜂窝掉下来,并被马.. 点赞2025-04-24 07:32 -
详细解析抬头纹多的人命运是不是不好
其实抬头纹是相当的常见,但一般都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出现抬头纹的,而有些人是年纪轻轻就有抬头纹出现的,这样不是很好的。如果出现了抬头纹很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的,容易有很多烦心事的,事业不能顺利,感情生活.. 点赞2025-04-24 07:30 -
孕妇梦见栗子有什么预兆 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做梦相信每个人都体验过,但是梦到的内容就是千奇百怪的。那孕妇梦见栗子有什么预兆?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孕妇梦见栗子有什么预兆:1、孕妇梦见买栗子,预示着近段时间内会有破财的征兆。2、孕妇梦见吃栗子,提醒孕妈.. 点赞2025-04-24 07:27 -
观音灵签63签解签学业
请问观音灵签的第63签怎么解签题:女娲氏炼石签文:昔日行船失了针,今朝依旧海中寻;若然寻得原针在,也费工夫也费心。出处:观音灵签签运:中签诗意:此卦海中寻针之象。凡事费心劳力也。故事:淮南子览冥篇。往古.. 点赞2025-04-24 07:26 -
梦见家门口有死人,吉凶指数差2分满分
周公解梦:梦见家门口有死人是什么意思:梦见死人,不用害怕,不一定是坏事。梦到门口,表示做梦者渴望友情和爱情。梦见死人还有一种含义,就是这个梦的确是一种警示。梦见家门口有死人,志趣不合的人,仍然可以成为.. 点赞2025-04-24 07:22 -
楠字五行凶吉
楠字五行凶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五行包括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不同的事物和属性。南字在五行中的归属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讨论南字在五行中的好运。楠字的五行属性首先.. 点赞2025-04-24 07:20 -
清明梦是不是灵魂出窍了,它和白日梦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人都是会做梦的,只是频率不一样而已,而且做梦的状态也有很多种,有一种就是清明梦,很多人说做这种梦的人是灵魂出窍了。清明梦是不是灵魂出窍了:清醒梦和灵魂出窍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清醒梦指的是在做梦的时候,人.. 点赞2025-04-24 07:19 -
脸上痣的图解,男人脸上十大福痣图片
男人和女人脸上都有痣是正常的。但是你知道脸上痣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吗?如何预测脸上的痣?接下来,让我们从痣的位置和命运中学习!1、泪堂有痣泪堂代表男女感情,泪堂有痣的人,一般都是感情不专一的人,想不出轨都.. 点赞2025-04-24 07:12 -
算命先生的神秘之道:他如何洞悉你家的人数?
**描述:** 你是否曾经好奇,为什么那些算命的师傅在没有见过你的情况下,却能轻松说出你家里有几口人?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看似神秘的现象,揭开其中的奥秘。---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街头或庙会里,与.. 点赞2025-04-24 07:12 -
八字火木命
八字火木命的人热情开朗,思维敏捷。他们有很强的创造力和积极的精神,在各行各业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1. 性格特点- 火木命的人通常热情、开朗、活泼,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轻松带动周围的气氛。- 他们不仅思维敏捷.. 点赞2025-04-24 07:05 -
妈祖灵签1一60签解签7
妈祖灵签1-100详细说明介绍母祖灵签证是中国道教中的一种占卜方式。自明朝以来,母祖灵签证被认为是一种非凡的邪教活动,但在台湾、香港和其他地区,母祖灵签证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崇拜。母祖灵签证由1到100个数字组.. 点赞2025-04-24 06:58 -
家里有树有蜜蜂好吗吗吉凶
蜜蜂入屋的迹象是好运和坏运。判断蜜蜂入屋是好运还是坏运气蜜蜂进屋的迹象通常是吉祥的,说明家里有幸福,也能反映出家里的风水不错。1、家庭风水:蜜蜂的生活条件非常苛刻。首先,它们应该有良好的照明,然后确保.. 点赞2025-04-24 06:52 -
7月12日吉凶时辰是什么
每个人都渴望在生活中掌握更多关于财富的秘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和邪恶理论为预测未来提供了深刻的方式。特别是在特定的日期,了解不同时期的吉祥和邪恶变化尤为重要。本文将深入分析2024年7月12日的吉祥和邪.. 点赞2025-04-24 06:45 -
乙木命理分析
前面我们解析了甲木命的特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今天我们分析乙木命的特征。亁造 丁亥 大运 8——18 辛丑壬寅 19——28 庚子 命宫:戊申乙丑 29——38 己亥壬午 39——48 戊戌49——58 丁酉59——68 丙申69——79 .. 点赞2025-04-24 06:38 -
艮山坤向兼丑未的吉凶
坐着很重要,但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山脉,是主要的,不在现场不是专家不能说,书本知识不能发挥作用,阴房子和阳房子有很大的区别,不能误导人,也许会伤害人!房子以向为重,以先天净阴净阳,纳甲男女搭配为吉。根山.. 点赞2025-04-24 06:37 -
北帝灵签46签解释白话文
婚姻很难有曲折,除非你先斩后奏,比如不让家人知道为什么先登记,明白吗,否则很难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不幸福。我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如果你有家庭婚姻(或者一方有家庭,你们相爱了),那就不要前进,即使你成为了这.. 点赞2025-04-24 06:30 -
李昕怡名字怎么样,昕怡这个名字怎么样
天格8的分析(八卦之数)八卦之数可以说是笔运乘势。八卦中的八卦既像路,也像根,行为成了八卦中的第一个。八卦中也有行为、行为、行为的女性,但大致都是行为的人。那么,什么样的名字会更容易成功呢?下面跟陈卿有.. 点赞2025-04-24 06:10 -
观音灵签63签问交易
人生就像一笔交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里不断地进行各种交易。有些交易是物质上的,有些是精神上的,有些甚至是命运上的。在观音灵签的63签中,讨论了生活中的这种交易。本文将以“63签字交易”为中心,深入探讨.. 点赞2025-04-24 06:02 -
最圆滑的三大生肖,榜首是:龙,勿深交,否则受害的是你!
最圆滑的三大生肖,榜首是:龙,勿深交,否则受害的是你!古语云:"圆滑者,如水之性,无棱角而善周旋。"生肖命理中,有三大属相以圆滑著称,其中龙居首位。与圆滑之人深交,恐有祸患。今日不妨细说这三大生肖的.. 点赞2025-04-24 05:59
微信分享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