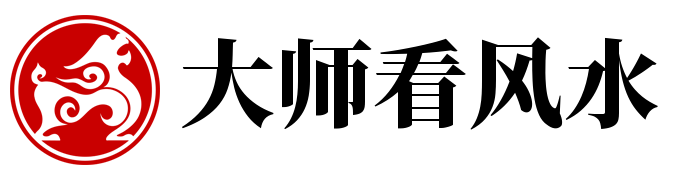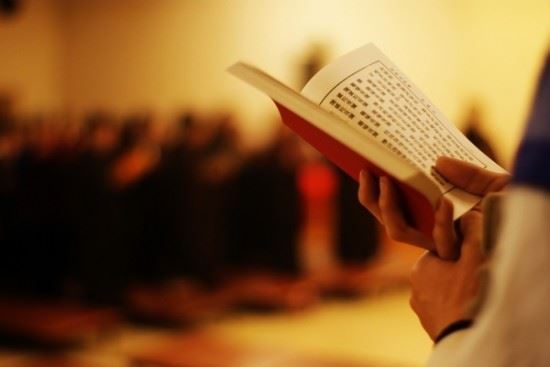王阳明:凡人无法领略圣贤的“极乐世界”,除非提升自己的真境界
一人一境界,那是人们真正能享有的,名利权势只是假象,小人享受不到君子美妙的内心体验,凡人无法领略圣贤的“极乐世界”,除非你提升自己的境界。
1.人生第一等事
【译文】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或许是读书学圣贤吧!
人生第一等事是什么?当然是立志。怎样立志呢?有人说,“我要当政治家”,“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企业家”……这并不是真正的立志。这家、那家,都只是个标签,挂上身上就有,取下来就无,很虚幻。后主刘禅是个政治家,夏桀王、商纣王也是政治家,那又怎么样呢?真正的立志是确立别人拿不走的标志,建立不倒的“品牌”。所以,人生第一等事是确立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按传统观念,由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人:
一是小人。他们是以损人利己为乐的人。有人说“伪君子”不如“真小人”,其实“伪君子”和“真小人”都是小人,只是损人利己的方式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不同。
二是愚人。他们是不知生为何来、死为何往的人,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满脑子偏见执念,观念很难改变。愚人未必是文盲,文盲未必是愚人。在愚人中,有相当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傻瓜。
三是庸人。他们是用身体思考的人,凭感觉生活,只想开开心心过日子,没有高尚、远大的追求。
四是君子。他们是很“爱干净”的人,他们讨厌自我思想的污秽,积极加强修养,理智地管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们是常人心目中品德高尚、可亲可敬的人,却会被小人嫉妒。
五是贤人或大人。他们是有大品德、大才能、大学问,能够成大器、办大事的人。即使没有用武之地,他们也往往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施加很大的影响力。
六是圣人。他们是了悟人生真谛,智慧通达、境界非凡的人。
一个人确定了要成为什么人,不管他做哪门学问,从事哪项事业,他的人生格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好比鸟入樊笼,无论怎么扑腾,都只能待在那么一块地方。除非他重新给出人生定位,他的自由空间才会增大。只有圣人能破笼而出,得“大自在”。
人们不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真实愿望隐蔽在潜意识中,自然地支配着人的行为。例如,有的人起初雄心勃勃,锐意进取,很有点“大人”模样,可一旦功成名就,便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因为他心里只是一个庸人底子,哪有大人的心量?
王阳明从小就明白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关于他的立志,《顺生录》记录了一个颇具神奇色彩的故事:那是他十一二岁时,一天,他与几位学友在长安街上漫步,遇到一个看相先生,惊奇地对他说:“我今天为你看相,你日后一定会想起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领这儿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
相士的话或许只是胡诌,对王阳明的暗示作用却是很大的,从此,“圣贤”二字就被他输入了大脑深处,“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十三岁时,有一次他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说:“唯读书登第耳。”教师的话似乎言之成理,作为一个读书人,参加科考,金榜题名,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吗?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他的父亲听说此事,笑着问他:“你想做圣贤吗?”
王阳明不好意思回答,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追求。当时宋儒的“格物致知”说颇为流行,而“格物”之意,二程和朱熹都认为是“穷事物之理”。王阳明一知半解,说干就干,邀请一个学友,对着竹子,不停地“格物”。到了第三天,学友用脑过度,只好放弃。王阳明嘲笑他心志不坚,继续坐在那儿“格物”。到了第七天,王阳明筋疲力尽,竟至晕倒,被人抬回来。这次“格物”失败,让他受挫不小,自我解嘲说,“圣贤有分”,不是人人可做。他的话,似乎表明他想放弃“学圣贤”的志向,而且此后他时而学道家的“导引术”,时而学佛家的参禅打坐,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应付科举考试,并考中进士。
但是,“学圣贤”的志向已经进入了王阳明的灵魂深处,他无论学什么、做什么,事后来看,都走在“学圣贤”的路上,都是在探索契入圣贤的方法。最后,他跳出程子、朱子理学之外,别出蹊径,开发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法门,并自豪地宣称这是“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他当然再也不会傻乎乎地“格”竹子了,因为他认为“格物”的真意是“正物”,心正则物正。
王阳明是否学成了圣人?难说!因为圣人是一种境界,只有“自家体会得”,别人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一位“大人”或“贤人”,因为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王阳明把人生目标定位到“圣贤”的至高境界,最后成为一代大贤,已经很成功了!
2.圣人不是靠聪明造就
【译文】一个人之所以成圣,在于纯粹地感悟天理,而不在于才能大小。因此,即使是很平凡的人,只要肯自修,使自己的心与天理契合,就可以成为圣人。
人人都有良知,都是“天生圣人”,只因后天的习染,变作了小人、愚人或别的什么人。阴沟里的金子还是金子,只是不那么好看,不那么好闻,价值却还在,洗净了还可爱。所以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
成圣的标志是“纯乎天理”,让“金子”变回本来的模样,一尘不染。
成圣的途径是“肯为学”。很显然,王阳明为学,不只是读书长本事而已,学问再高,本事再大,都不一定能“为圣”。对此,王阳明解释说:“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
人心如纯金,人欲多一分,成色减一分;人欲减一分,成色增一分。做学问、长本事,只能增加分量,不能增加成色。分量足当然是好事,成色太差,跟铜铁等价,就无趣了!
王阳明指出了一条“为圣”的坦途:去人欲而存天理。将后天的人欲一分分减少,直至“无欲”,回归天性,回到最初的原点,便成圣了。
许多人觉得“无欲”二字不可思议,也不以为然:难道孔子、老子不穿衣吃饭吗?不娶妻生子吗?不想做官、赚钱吗?这当然是对“无欲”的误解。打个比方,水往低处流,流过山峰,流过平原,流归大海。那么,水有没有欲望呢?如果没有,为什么忍不住向低处流的冲动?如果有欲望,为何不向高处流,流到银河去?很显然,水无所谓有欲或无欲,只是自然而然,按自己的本性行事。圣人也是如此,无论吃饭穿衣、娶妻生子、做官发财,都顺从本性、自然而然,像不一样,在有欲无欲之间,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这就是圣人的“无欲”。
常人却不同,明明是小鸡,却要吃老鹰;明明是丑小鸭,却要扮白天鹅;明明只有二两饭的胃口,却要叫满汉全席。这就是贪欲了!
自然的欲望是“无欲”,不自然的欲望是贪欲。那么,怎样区分自然或不自然呢?此意不可说,只能自去领悟。
王阳明还指出了一条“为圣”的方便途径:“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你只要有爱心、做善事,一心一意,不愧不悔,迟早可入圣贤之门。
“善欲”不是“无欲”,但接近“无欲”。你始终保持善欲,喜欢帮助别人,喜欢看见别人摆脱烦恼、困境,这是很高的境界,但离圣境还远,因为你的善欲还可能退转,转到相反的方向。举个例子,不久前,曾发生过一起争议纷纷的新闻:几个善士捐资助学,以一帮一的形式,给几个青年学子提供学费、生活费。
这几个学生接受了馈赠,一年多时间都不曾写信给“恩主”道一声谢,于是,几位善士不高兴了,将此事透露给了媒体,不用说,那几个学子受到了众口一词的指责。可以想象,那几个学子所蒙受的损失远比他们得到的馈赠大,因为他们背负着“忘恩负义”名声,心灵的创伤也会陪伴他们很长时间,甚至影响他们一辈子。反观几位善士,起初善欲很强,后来善欲却变成了恶念,他们向媒体透露此事,等于向那几个学子实施了报复,根本没有考虑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后果,等于由圣道入魔道了。
按佛家的观点,善心永不退转,才入圣道。怎样才能如此呢?当你切身体验到帮助别人不是在帮助别人,完全是在帮助自己;愉悦别人不是在愉悦别人,完全是在愉悦自己,你的善心就不会退转了。那么,当你做了善事,帮助了别人,会由衷地高兴,根本不会冀图别人的感激、报答,更不会为别人没有一声“谢谢”而愤愤不平。
但这不是说“善欲”没有用,一旦你经常发善心、做善事,体验到了其中的乐趣,你就有可能领悟“人我不二”的真谛,由此契入圣道。
王阳明早就领悟到圣贤和凡夫俗子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各人的功夫,任何一人肯下工夫,都可能成为圣贤。所以,他看人都带着看圣贤的眼光,以平等之心待,不太在意世俗的尊卑贵贱。当他谪居龙场驿时,真诚地对待自己的随从们,为他们熬药、煮粥。大家觉得他是“大人”,被他服侍受当不起,他安慰说:你们跟随我一路走来,吃了许多苦。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你们不就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吗?
对当地夷民,汉族人一般会有歧视心理,认为他们是“野蛮人”。王阳明却毫无歧视之心,因为他们也是“天生圣人”。他说:“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
虽然语言不通,他跟夷民们的关系却处得很好,交了很多真心朋友。他时常出没于丛林、山洞之间,同夷民和流亡至此的汉人谈天说地、讨教风俗,并指导他们伐木建屋,替他们排忧解难。很快,当地居民都把他看成能人、友人、神人,对他尊敬有加,还自发地帮忙,为他建起了一座大屋。后来,此屋便成了著名的“龙冈书院”。
一个人能认识到人人都可能为圣贤,而以平等之心对待每一个人,离圣贤之门已经很近了!反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自以为应该高居别人之上,离圣贤之门已经很远了!
3.圣人无善无恶
【译文】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有善有恶是思想的萌动,知善知恶是人的良知,培善去恶是格物的功夫。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有一个等式:心=性=理=良知。
虽然是一个等式,每个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
心是什么呢?心=无善+无恶=0;
性是什么呢?性=有善+有恶=0;
理是什么呢?理=非善+非恶=0;
良知是什么呢?良知=知善+知恶=0。
善恶可以说一正一负,但流于观念上时,其性本空,只是一个0。正因为如此,格物便成为可能。假设恶念像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是实体的存在,你想格掉它,哪怕你有愚公精神,这辈子也不能够,还要靠子子孙孙帮忙。因为恶念本空,你想格掉它,马上就格掉了。格物也可以列出一个等式:格物=为善+为善+为善+为善……
为什么要格物呢?因为人有贪欲,以至失其本心,变为凡心。
凡心=为恶+为恶+为恶+为恶……
所以,需要不停地格物,使凡心渐近圣心。
圣心无善无恶,只是一个0,如同佛家所说的“空”。但“空”不是没有,正如0不是没有一样,不然,将你的存折上拿掉一个0,你就该哭鼻子了。
由于王阳明所说概念似同非同,所以闻者似懂非懂,为这些问题,王阳明跟弟子们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有一次,弟子德洪与汝中在一起讨论学问。汝中谈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德洪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
汝中说:“这恐怕不能算绝对结论。如果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说意有善有恶,那么心体必然也有善恶在。”
德洪说:“心体是天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人心会受外物感染,意念上就有了善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的正是回复心体、天性的功夫。如果意念没有善恶,做什么功呢?”
当天晚上,二人向王阳明请教。王阳明说:“二位的见解正好相互补充,不宜各执己见。我这里点化人原本有这两种方法,悟性高的人可以从本源上直接悟入。人心本体原本是明莹无滞的,在发而未发之间。悟性高的人一旦悟到本体,即是功夫,他人、自我,内心、外物,可以一齐悟透。悟性较次的人,难免有个习染心,本体受到蒙蔽,因此教他在意念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功夫精通后,尘埃去尽之时,自然可以明了本体。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接引悟性高者的法门;德洪的见解,是我为悟性较次的人所设的法门。二位互补,可以接引上中下各色人入道,如果各执己见,眼前便会失去求道人,而且在领悟上都有未尽之处。”
王阳明的话,跟佛家所用法门相似,见解也一致。无论善恶观念,以及烦恼、痛苦等,都是空性,悟性高的人可以直接从空性悟入,一旦悟到它们只是一个0,心便清净了。悟性较差的人认为善恶观念是有,烦恼、痛苦也是有,好像有个东西堵在心里一样,那就要做格物功夫,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格掉。但善念有益无害,用不着格掉,反倒可以加强。当功夫做到一定程度,有可能悟到其性本空,即使悟不到,有一腔善念总是好的,不能为圣贤,也能为君子了!圣人无善无恶,“从心所欲”,高高兴兴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做的全是常人认为的善事,如果你带着善念做善事,做的事其实跟圣人一样,只不过你认为这是善事,圣人却不认为是善事,区别只在内心体验上。
还有一次,王阳明带着弟子在花园里除草。薛侃忽然大发感慨说:“天地间的事真是不可理解,为什么善总是难以培育,恶却又难以去除?”
王阳明说:“因为你没有培育,没有却除。”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这样看待善恶,一起念便错了。天地之间,花草都是生命,岂有善恶之分?人要赏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一旦要用草,草又成了善的。所以,事物的善恶,皆因人的好恶而生。”
薛侃不服:“如先生所说,世间没有善恶之分了?”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侃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阳明说:“佛家立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事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侃问:“草既非恶,那么草不宜除掉了?”
王阳明说:“你这便是佛氏、老子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侃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阳明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刻意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有好恶一般。”
薛侃问:“就除草这件事来说,怎样一循于理、不着意思呢?”
王阳明说:“草有妨碍,理应除去,那就去掉罢了。偶尔没有拔除,也不累心。如果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侃问:“按您的说法,善恶全不在物上了?”
王阳明说:“只在你心上,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侃说:“说到底物还是无善恶。”
王阳明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侃问:“那又该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阳明说:“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该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侃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一分个人的意思?”
王阳明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廓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
王阳明有些不耐烦地说:“这个问题,你该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个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是什么心?”
最后,王阳明总结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在上面的谈论中,王阳明已经将“无善无恶”的问题讲得很清楚了,能不能理解,全看各人的悟性。很多人听了可能会更糊涂,因为他们理解事物时,往往不能依循一定的标准,而是不时地变换标准,一会儿从道德、法律的角度看问题,一会儿从人我的立场看问题,一会儿从切身利益看问题,而且头脑中的概念不时变换,常犯“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王阳明以“无我”之心,始终站在“天理”的角度看问题,你必须以此角度,才明白他说了什么。
4.修身俟天命
【译文】如果有人说“生和死、短命和长寿都有定数,我只是一心向善,修养自身,以待天命而已”,这是他平日尚不知道有天命。顺从天命,虽然天、人分为二体,倘若已经知道天命之所在,只需恭敬奉承它就行了;如果还要“待天命”,说明还不知道天命之所在。
真正的悟道,按佛家的观点,在于“明了生死大事”。王阳明也认为,如果在生死问题上“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命之学”。凡人心里塞着一个大大的“我”字,把这条命看得太重,并且认为,活着时的享受才是真的,一旦死了,一切便与自己无关。
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占有和享有,一切烦恼、痛苦都因此而生。得不到时为得不到痛苦,得到了却又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痛苦。只有明了生死大事,悟到了生命的永恒,活到可生可死的境界,烦恼、痛苦才会解除。正如老子所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王阳明认为“吾心即宇宙”,心与天理不二,那么天命岂不是在自己心里吗?所以他不认同“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这句话。
但“修吾之身,以俟天命”确实是一句得道的话,跟王阳明的意旨也没有不合之处。王阳明将“俟”解释为等待,但“俟”字含有顺其自然的意思,并无所执。无论顺应“天命”或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天理”、“性”,都是一个意思。
王阳明认为,人不应该太看得生死而要顺从天理,他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婉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王阳明这些话,大概只能算是“方便说法”,拣别人听得懂地说,因此有所滞着。这也无可奈何,对那些没有“明了生死大事”的人谈生死,如同对牛弹琴,怎样都谈不通。
“明了生死大事”不容易,有时需要经历生死考验才“见得破,透得过”。生活中,有些人把自己的命看得不值钱,无故冒生命危险,甚至自寻死路。他们也许真的不怕死,但他们怕活,跟怕死其实没有两样,都是“魔障”,跟悟道者的通透大不一样。悟道者不怕死也不怕活,不怕幸福也不怕痛苦,他们把生命看成无价之宝,到了需要交出去时却又毫无留恋。若问他们的境界,只是修身俟天命而已!
王阳有的悟道,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当时,奸宦刘瑾等“八虎”乱政,老臣刘健、谢迁等人联合言官们上奏明武宗,请诛刘瑾,被刘瑾诬为奸党。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请求留刘健、谢迁,被刘瑾逮捕,廷杖除名,打入大牢。时年37岁的王阳明不避祸患,毅然上书援救。刘瑾大怒,将王阳明廷杖四十,死而复生,又罚跪于金水桥,然后下狱审判,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王阳明去龙场驿途中,刘瑾尚不甘心,派人追踪在后面,企图加以暗杀。王阳明意识到了危机,到了钱塘江边,留下一首《绝命诗》,又取下鞋帽,放在岸边,制造投江自杀的假现场。跟踪者信以为真,拿着鞋帽和《绝命诗》回京复命去了,王阳明侥幸逃过了追杀。
但他的危机并未过去,当他搭乘商船行至舟山时,飓风大作,商船漂泊到闽北。他登岸进入武夷山,晚上想入一座寺庙求宿,寺僧却不肯收留。他只好暂宿在一座无人的野庙中,不料这正好是老虎栖息的巢穴,夜半时分,老虎回到野庙,见一人伏睡香案,绕廊大吼,却不敢入内。第二天,寺僧以为王阳明必已葬身虎腹,来取他的包裹,却见他伏案未醒,料知此人不是常人,于是请入寺中,殷勤招待。
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80里许的修文县城区,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虫索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阳明刚到这里,既无住房,又无粮食,只好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他自幼长于高官贵戚之家,养尊处优,突然面临如此恶劣的环境,苦楚又倍于常人。更不幸的是,他还患了虚痨肺病,生存更觉艰难。他深知随时都有倒毙荒野的危险,“自计行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但他的性格是,越是害怕什么,越是迎头而上。于是,他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说:“吾惟俟命而已!”从此,他经常躺在石棺材里,努力对抗怕死的念头,“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诗谈笑,故作潇洒。
一天夜里,他忽然觉得“心中洒洒”,仿佛有人对他说话,于是“大彻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他又以平时背熟的“五经”来印证他彻悟的一切,莫不吻合。从此,他不仅悟了圣人之道,也对生死大事洞然明白,进入了无忧无畏的境界。
佛祖曾说:生命在呼吸间。一呼一吸中,包含着一生一死的异数,很悠长也很短暂。人应该用这或长或短的生命干什么呢?吃喝玩乐都是幻景,功名利禄都是烟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呢?弄清了这个问题,或许就能明了生死大事了!
5.“戒慎恐惧”即是良知
【译文】能够戒慎恐惧,就是良知了!
如今的人经常高喊“自由”,但是,什么是自由?很显然,你可以按自己意愿说话、办事、思考,你就享有自由;你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敢说,你想做的事受到他人限制,你就不得自由。
那么,自由是谁给予的呢?有人以为是别人给予的,不自由的原因是别人造成的。员工厌恶老板不给行动自由,学生厌恶老师、家长不给表达天性的自由。事实上,自由主要靠自己给予,良知才是自由的真正主宰。你讲道德、讲规则,凡事与人为善,所言所行都受到大家欢迎,那么,你爱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他人和政府为什么要限制你的自由呢?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他想做的事正好都符合道德规范,不符合规范的事他从不想做,所以,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从来不需要向政府要求“言论自由”。
反之,你乱说乱动,自由就要受到限制了。阿Q梦想“想什么就是什么,想谁就是谁”,这样的自由能给他吗?他恃强凌弱,欺负小尼姑,还说什么“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这样的自由他应该享有吗?他可以有“恋爱自由”,但他不讲恋爱规则,搞“性骚扰”,拉着吴嫂想“困觉”,结果被赵太爷用“哭丧棒”揍了一顿。不自由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想拥有不该拥有的自由,这是真正的不自由。
真正自由的人,服从自我良知的管理,以“戒慎恐惧”为修养。“戒慎恐惧”出于子思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大意是:害怕做错事,即使别人不见;担心说错话,即使别人听不见。王阳明对这句话备极推崇,经常拿出来跟学生讨论。他说:“君子戒慎于不睹不闻,省察于莫见莫显,使其存于中者,无非中正和乐之道。”你用不着别人来判断你做得对不对、说得对不对,你只要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不管别人能否看见、听见,你坚持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内心自然“中正和乐”。
有的人不然,人前人后不一样。老板不在时,随便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老板来了,便装成勤奋工作的模样;跟老板说话时,一脸敬畏,一副“好孩子”的模样,转过脸,便一脸轻蔑,哼道:“有什么了不起?换个位置,我比你强多了!”这样的人多么不自由!他想做的事、想说的话正好都是不能做、不能说的,内心岂不烦恼丛生?
一个人不知戒慎恐惧,只会随流性转应付环境,他就成了环境的奴隶;一个人服从良知,他才是自己的主宰。
有一次,许衡和几位朋友冒着酷暑赶路。到了中午,他们又渴又饿,却无处可以买吃的。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百姓四处逃散,方圆百里之内,十室九空。后来,他们来到一个村庄,里面的人全跑光了,但路边有一棵梨树,树上果实累累。同伴们大喜,争先恐后地爬到梨树上摘梨子吃,许衡却在树下正襟危坐。同伴们诧异地说:“你等什么?快上来吃梨子吧!”
许衡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同伴说:“乱世的梨子,早就没有主人了。”
许衡正色道:“梨子没有主人,难道我心里也没有主人吗?”
许衡终究没有吃这些梨子。
许衡不愧是一个懂得“戒慎恐惧”的人,他怕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良心。当他无条件服从心中的“主人”时,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智慧是清明的,他的言行也必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他成为一代宗师,是元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一个人只有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做正确的事,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戒慎恐惧”看似自我设限,得到的却是自由。好比走路,人眼前始终只需要一条路,用不着惦记每一条路。你以戒惧之心,约束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任何地方。那不是真正的自由吗?
6.随人欺慢,处处得益
【译文】人如果实实在在地用功,任由别人怎样诋毁、诬蔑,任由别人怎样欺侮、怠慢,处处都可以得益,都是培养道德的资粮。如果不用功,别人的诋毁、诬蔑、欺侮、怠慢都会变成“魔障”,终究会被它们累倒。
王阳明一向推崇“动忍增益”的功夫,其要旨类于佛家“忍辱”的修养。佛家所谓“辱”,包括身心所受任何苦楚,忍辱即忍一切苦,把这项功夫做好了,才能得一切乐。王阳明所谓“辱”,主要指外人施加的窘辱。
“动忍增益”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动忍”,对别人的窘辱要忍得住。他说:“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
但是,忍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佛不一定喜欢争一柱香,人却喜欢争一口气,自己没做错什么,却被别人说闲话,被别人嘲笑、侮辱、毁谤,这口气如何咽得下?俗话又说:“人要脸,树要皮。”被人耻笑、非议,丢脸了,这脸面不找回来如何做人?
“忍辱”不易,怎么忍呢?你需要做功夫。一项功夫是“抗打击”功夫。拳王之所以成为拳王,不仅因为他能打,也因为他能挨打,对方的拳头打在脸上,晃晃脑袋,没事!这功夫一定是平时挨了不少打练出来的。你要成为心灵的拳王,平时应该多挨打。宋朝的寒晦禅师和拾得禅师是好朋友,有一次,寒晦问拾得:“人家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蒙骗我,应该如何应对?”拾得说:“只可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拾得所说的,就是提高“抗打击能力”的方法。有的人被别人一句话就激得跳起来,乃至寻死觅活,摸刀杀人,这功夫太差了。别人招惹你或许不对,但你被人一指点倒,还因为自身太弱,不过是个“心灵婴儿”而已!那么,你应该把窘辱你的人当免费“陪练”,使心灵变强。
一项功夫是“慈悲喜舍”功夫。这是佛家的上乘功夫。别人窘辱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你做错了什么而不自知,也许你没有做错而对方理解错了,自招其病,值得你同情而不是愤恨。打个比方,一个病人痛苦不堪,大喊大叫,大哭大骂,当此之时,你是什么感受?你应该庆幸害病的不是自己,即使挨了骂,也该知道对方的骂声其实不是骂声。同样的道理,别人无故窘辱你时,内心一定正受到欲火、妒火、怒火或其他种种邪火的焚烧,心里病得很重,以至言行失控,跟感冒发烧说胡话一样,你又何须计较呢?
第二个要点是“增益”。当你把“动忍”功夫做好了,自然受益非浅,正如王阳明所说:“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但王阳明并不满足于“力”的增长,还要求通过“动忍”,将别人的“毁谤”、“欺瞒”变成“进德”的资粮。
《永嘉真觉禅师证道歌》说:“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目疲。我闻恰似饮甘露,销钅容顿入不思议。”别人的毁谤、非议怎么可能“甘露”呢?其实,无论别人赞美你也好,非议你也好,都只是一句话,你将一句句话染上了颜色,才影响了你的心情。好比下雨,是一种自然现象,你强自分成好雨、苦雨,心情便变得不同了。你若以自然之心看待别人的话,不认为那是毁谤、非议,那么,你通过别人的话,得到的就是真知而不是坏心情。
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服装商人,卖的都是名牌时装。但顾客时常会“毁谤”、“非议”说,“这件衣服的颜色太差了”,“太贵了,根本不值这个价”,“款式太旧,卖给‘50后’还差不多”……当顾客“胡说八道”时,你若跟他们怄气,那就太傻了。一方面,“嫌货才是买货人”,顾客对你的衣服提出不满,说明他们很感兴趣,否则何必多费口舌?一方面,顾客的零言碎语中,透露了许多宝贵的信息,你若善于分析,就可以了解不同性别、年龄的顾客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所以说,这些“嘴臭”的顾客正是你的好顾客,你可以通过他们大获其益,你正应该爱他们,怎么可能恼恨他们呢?
在生活中,对你没好处的只是那些跟你做了十年邻居却不知道你的名字的人,那些“毁谤”、“欺慢”你的人,都是你的“潜在顾客”,都可能有益于你,关键看你有没有“增益”功夫。
王阳明的“动忍增益”功夫做得很好,虽然“毁谤”、“欺慢”几乎伴随他一生,他总能得其利而避其弊,使自己的德业、事业双获丰收。
王阳明谪居贵州的龙场驿时,是他一生最倒霉的时候,他却将之变成了幸运的开始。驿站主要负责来往官员、信使的接待工作,相当于官方招待所、邮电局,龙场驿地处万山丛中,一个月都难得搞一次接待工作。王阳明有大量空闲时间,于是开设龙冈书院,免费给爱学习的人讲学。慕名而来者很多,他因此名声大噪。龙场驿属思州管辖,思州太守不知为了耍威风,还是嫉妒王阳明的名声,无故派人前来捣乱。当地群众看不过意,自发组织起来,将那些公差打走了。
思州太守更是恼怒,上告王阳明不服管教、聚众闹事。思州按察副使毛应奎是王阳明的余姚同乡,担心他受害,于是出面斡旋,劝他去向太守赔个不是。此时,王阳明还没忘了按良知做事,一方面,他认为当面道歉不合情理,只会助长对方的歪风邪气;一方面,他却又愿意做一回“矮子”,给太守一个台阶下。于是,他给毛应奎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陵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恨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
他表明,跪拜太守,是他这个小官应尽的礼仪,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太守没错,自己也没错,如果道歉,反见得双方有错了。接下来,他又写道,自己“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言下之意,到了这种地步,怕死也无益,太守如果不依不饶,他也没有办法。
结果,“太守惭服”,再也不来找王阳明的麻烦。而当地的秀才、卫所官员更是仰慕他的为人和学问,纷纷上门求益。安宣慰还派人送来米、肉、仆役、金帛、鞍马等,王阳明只收下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余的都逊谢不受。
王阳明受到太守的“欺慢”和“毁谤”,他本着良知不动心,得体地处置,结果坏事变好事,他的处境反倒比以前好多了,名声也比以前更大了。
《佛遗教经》说:“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一点羞辱都不能忍,像爆炸一样一点就炸的都是小人物,那些能够“忍辱”的人,才可能成为有大智慧、大才能的人,才可能办成大事,成为大人物。所以,对人生事业来说,“忍辱增益”的功夫很重要!
7.招灾惹祸的四大原因
【译文】灾祸没有比贪占天然的功劳更大的,罪行没有比掩盖他人的好处更大的,过恶没有比剽窃下属的才能更深的,侮辱没有比忘记自己的羞耻更重的。如果四者皆备,引起灾祸的全部条件便成熟了!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功莫大焉,嘉靖皇帝诏令“王守仁封伯爵,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照旧参赞机务”,不久后,又诏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王阳明接到诏命后,没有欣喜若狂,没有自鸣得意,而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当即上了一道奏疏——《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言辞恳切地请求皇上废除对自己封赏的恩典。在奏疏中,他留下了一段经典名言:“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王阳明认为,平叛成功,一是时势使然,二是大家的努力,并非他一人之功,因此不宜独受大赏,否则就是“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袭下之能”而“忘己之耻”了,否则就会自招其祸。
王阳明是惺惺作态、故作谦逊吗?好像不是。他心体“良知”,对这件大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奏疏中,他一一分析了不敢受封的理由。
何谓“叨天之功”?他说:“宁藩不轨之谋,积之十数年矣,持满应机而发,不旬月而败,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厌乱思治,将启陛下之神圣,以中兴太平之业,故蹶其谋而夺之魄。斯固上天之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王阳明的话很有道理,当时明朝国运虽已渐衰,官场腐败昏暗日益严重,但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程度,希望“变天”的人属于少数,宁王朱宸濠点起了反叛之火,却缺少“柴草”,难以燃起燎原之势。表面看,局势由少数精英左右,实际上,国运从来都由广大民众主宰。但是,只有王阳明一流智者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何谓“掩人之善”?王阳明说:“先宁藩之未变,朝廷固已阴觉其谋,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权,使据上游以制其势。故臣虽仓卒遇难,而得以从宜调兵,与之从事。当时帷幄谋议之臣,则有若大学士杨廷和等,该部调度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等,是皆有先事御备之谋,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今诸臣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
王阳明将功劳归于上级领导的“英明决策”,虽有过誉之嫌,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阳明,并力劝朝廷给予阳明便宜行事的权力,使阳明在平叛过程中能随心所之,不受掣肘,又在朱宸濠即将发动叛乱时,有意“大材小用”,调阳明去福建平定一个下级军官的哗变,使阳明躲过了朱宸濠的挟持。可以说,没有王琼的支持和保护,王阳明自身性命尚且难保,哪有成就大功的机会?
何谓“袭下之能”?王阳明说:“变之初起,势焰火昌炽,人心疑惧退沮。当时首从义师,自伍文定、邢王旬、徐琏、戴德孺诸人之外,又有知府陈槐、曾王与、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及杨材、王冕、顾亻必、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诸人臣今不能悉数,其间或催锋陷阵,或遮邀伏击,或赞画谋议,监录经纪……夫倡义调兵,虽起于臣,然犹有先事者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赖于众,则非臣一人之所能独济也。乃今诸将士之赏尚多未称,而臣独蒙冒重爵,是袭下之能矣!”
王阳明在奏疏中,指出了很多智勇之士的功劳,表明平定叛乱,全靠大家努力,功劳也是大家的。事实也是如此,成就任何事业,都要靠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无论领导或下属,都只是一台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失灵,便会影响全体;而功劳也不能尽归于某个“重要零件”。但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做到“按劳付酬”,好处往往尽归于那些领军人物,这是大家心理上基本可以接受的“分配方式”,但未必公平合理,永远有改进余地。许多独领功劳而大受其益的人,不知自己侵占了他人的功劳和当得利益,反倒沾沾自喜、自夸自傲,未免恬不知耻。王阳明作为受益者,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难能可贵;能坦然地讲出来,其精神境界确实令人敬佩。
何谓“忘己之耻”?王阳明说:“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当为。况区区犬马之微劳,又皆偶逢机会,幸而集事者,奚足以为功乎?臣世受国恩,碎身粉骨,亦无以报。缪当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鳏旷,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逾分。且臣近年以来,忧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聋,无复可用于世。兼之亲族颠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贪进,据非其有,是忘己之耻矣!”
王阳明认为,为臣尽忠,为官办事,只是本分上的事,办好了谈不上功劳,况且自己身体不好,应该有自知之明,退休回家;况且父亲老病,自己也该回家尽孝,如果贪图封赏,急功冒进,那就是无耻了。
王阳明能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只是“臣子之分所当为”,难能可贵。在现实中,对官员的要求往往很低,“不作为”是很多官员的基本作风,什么也不干,“一张报纸一杯茶”混一天,也没有关系,偶尔做了一件分内之事,就成了功劳,可以厚颜无耻地在报告中向上级表功,还可以恬不知耻地向当事人讨贿赂。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做分内的事,却要求分外的利益,医生“割开肚皮要红包”,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诸如此类,跟王阳明比,太没“良知”了!
王阳明此次上疏推辞封赏,未准;后来再度上疏辞封,仍不准,皇上还是将他该得的封赏给了他,论实绩,他的功劳毕竟很大。
但王阳明跳出自身得失之外,凭“良知”说话,确实说出了祸福的基本道理:人生最幸福且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做自己该做的事,赚自己该赚的钱,过自己该过的日子,享自己该享的福。如果拿不准当得不当得,不妨学学王阳明,争低不争高,争少不争多,亦不失为避祸良方。若是起了贪婪心,希求不当得之名利权势,离灾祸就近了,即使不受明里的损失,也必遭暗里的报应,伤身伤心伤神,甚至留下遗毒,害了儿孙。那又何必呢?
发布于 2025-03-29 06:27微信分享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微信或朋友圈